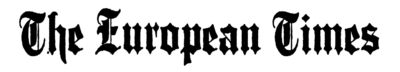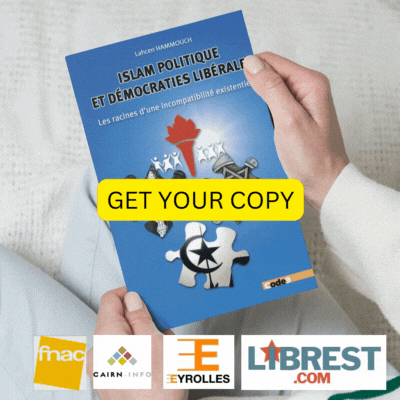鲍里斯·维舍斯拉夫采夫
在他的伦理活动和判断中,人无权采取天意的观点。 他无权判断sub specie aeternitatis [从永恒的角度],挪用上帝的观点,好像他和他坐在宝座上一样。 否则,他可能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太阳,同样照耀着好人与坏人。 开始允许和容忍邪恶作为自由意志的表现,就像上帝对人类所做的那样。 它甚至可能开始肯定邪恶在世界悲剧发展中的必然性,它在上帝的道路上的合理性。 最后进入反派和叛徒的角色,相信这个角色在造物主和他的天意预见和意图的世界悲剧中是必要的。 而越是可怕,为了庆祝正义和正义,为了庆祝天意而表演它的演员的谦卑、自卑和自我牺牲就越大。 这就是犹大的角色。 “Beata culpa” [blessed guilt] 根本不是过错,而是一种优点,但如果犹大能够预见上帝的道路,并有权站在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即非常普罗维登斯。 使徒保罗意识到了这些辩证的困难,并提出如下问题:如果罪人的不公义最好地彰显了他们的公义和公义,他们怎么能受到惩罚? “难道我们不应该做恶以致善吗?” (罗 3:8)。
如果诱惑必须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就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把它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尽管知道不为那个角色而生会更好(主观地,而不是客观地)。 事实上,没有比“应该”和“应该”更离谱的歧义,更离谱的 quaternio terminorum [四个术语的谬误,即演绎逻辑谬误]。 在一种情况下,这是对历史命运的天意的判断(诱惑必须来到世界上),在另一种情况下,这是对人的道德责任,关于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终任务的判断:他必须采取责怪自己。
然而,这不是逻辑谬误,也不是诡辩:整个问题显然包含在强制性的两个方面。 1)天意的神圣必要性和 2)道德行为的人类必要性。 在他的道德义务中,人无权站在天意意义上的义务的观点,从历史必然性或绝对精神发展的必要程度的观点出发。 它无权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立场(即“绝对精神”的立场)或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立场。 他这样说同样粗俗和不道德:在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得更好,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 因为它意味着将历史的罪行——例如革命的暴行——作为自由发展的必要阶段进行辩护。 如果“一切都变得更好”,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这种思想也可以从反面得出:人不能站在天意和绝对判断的观点上,即使后者符合人类对善、恶和正义的理解。 例如,他对复仇的渴望,想要消灭恶棍,不能被解释为对神圣复仇的要求。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句话听起来:复仇是我的,我会报答的。 上帝以另一种方式奖励,而不是当时,也不是我们想和想要的地方。 我们绝不能像约瑟夫·德·迈斯特那样,将刽子手的行为与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愤怒相结合,以此为刽子手辩护。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个刽子手都比每个恶棍更可恶,因为他将无误的认可、天意的认可和“客观精神”归于自己,而恶棍却在自己身上带着明显的罪恶印记和犯罪,这是更谦虚和——真实的。
人既无权进行可怕的判断,也无权预见它。 杂草的寓言证明了这一点:“客观上”对他来说似乎微不足道和不必要的东西不能为了实现绝对正义而被摧毁(例如,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邪恶的老妇人,总的来说,整个问题伟大的人物履行上帝的旨意)。 作为一个可怕的判决,绝对正义不是通过我们,而是通过它的绝对仆人——天使来行动。 这是通过比喻来揭示的。
这样,就好像它本身就得出了以下结论:渗透到天意的神圣计划不会为任何事情辩护,也不会因人们的行为而谴责人们,不包含任何人类学,因为邪恶仍然是邪恶的,它不应该是“正当化”,即因为天意没有好的和必要的计划而成为一种权利。 而且,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通向最好的恶变成了大恶; 导致“进步”和公正制度的邪恶是最坏的邪恶——一种敢于通过想象自己是善来为自己辩护的邪恶。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义的不是恶,而是从恶中衍生出来的善被妥协了。 不是目的证明手段是正当的,而是手段谴责目的。 历史进程的任何目的论合理化都是不道德的事业。
理性主义神义论在道德上不适合人类。 但它适合上帝吗? 毕竟,它是否提供了“神明的理由”?
NA Berdyaev 在卷中关于神义论的非凡文章。 本刊7篇。 它包含两个主要思想:
1. 否认虚假的神学、抽象的一神论,否认有一个静止的、幸福的、Eleatic 和非悲剧的上帝,创造世界和其中的所有悲剧,同时保持孤立和无情。 这样的上帝不应该被称义——这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主,无神论对他来说是正确的(第 56-57 页)。
2. 确认一个可能的神义论,作为上帝自己的悲剧,作为上帝的牺牲——上帝的苦难,上帝的激情。 上帝是爱,上帝是自由,而爱和自由是牺牲和苦难。 当然,这样的概念以基督的上帝人性和人的神性观念为前提。
这里提出的积极神学在什么意义上? 正确——只有一种方式:上帝得到保护,免于“为自己留下幸福,为受造物留下苦难”的责备(第 55 页)。 在这里,上帝爱人并与他一起受苦。
这样的决定可以被认为是详尽无遗的吗? 在消极方面,这似乎是一个强烈的想法:与世界隔绝的完美是不可能的。 与世界并存的完美存在于邪恶之中,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原始来源和创造者的能力中,当然,它是不完美的。 如果它(完美)为它的自给自足而高兴,它对它来说越糟糕,它就越不完美。 当然,这里的完美就是完整和完整(τέλος 和 πλήρωμα),它不能在自身之外留下任何东西,它必须把一切都放在自己身上,并在自己内部接受。 完美必须在内心接受,才能包容世间所有的邪恶、苦难和悲剧。
但困难来了——完美中充满了不完美! 满满的缺憾! 神,将邪恶带入自己! 终于受苦,垂死,经历悲剧! 所有这些负面价值(邪恶、痛苦、死亡)最终都包含在绝对善的正面价值中——作为完美的上帝! 但是,受苦受难的上帝不是绝对矛盾的吗? 悲剧的类别适用于上帝吗?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受苦的上帝”以及上帝和人的悲剧的想法。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悲剧都是神圣的人性,根本没有其他悲剧在其自身的意义上。 可悲的是,人永远与神联合,永远与神分离(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永远带着神圣和神圣,永远堕落和失去。 这就是理想世界、观念的本质。 (“Sie ist nur da, inwiefern man Sie nicht hat und sie entflieht, inwiefern man sie fassen will” – Fichte)。
柏拉图的爱神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神人”,因此是悲剧性的,他的命运就是普赛克的悲剧性命运。 上帝与人性结合是可悲的,人与上帝结合是可悲的。 完全没有悲剧,就是人与神分离,人不怀疑神的绝对自足,神不看人的绝对自足。 在不相容的混合和连接中隐藏着悲剧。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诺斯替教的巴西利德来说,世界进程的悲剧以绝对的分离、天体的孤立而告终:与上帝分离的存在不会受苦,因为它被包裹在“无知的面纱”中。 [1 ]
苦难和悲剧的根源在于无所不在的合一。 如果我们不把对立面放在一边,不把它们用线连接起来(柏拉图),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合二为一,就不会有不相容、矛盾、悲剧的现象。 悲剧性的矛盾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述:恋爱中的敌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无辜的内疚(俄狄浦斯),值得生命和幸福的毁灭。 但主要的悲剧是对无罪和无辜者的指控和惩罚。 可以说,这场悲剧是无法忍受的,问题来了:上帝如何容忍它? 这里重新提出了神义论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会变成悲剧?
要回答,我们首先要看到,世界是真实的悲剧,体验并直观地洞悉悲剧的本质。 有必要证明世界是一场悲剧,生活是一场悲剧吗? 道德经验使我们相信整个世界都在邪恶中,但世界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是美丽的,一切被创造的,一切真实存在的,都太好了。 这是人类精神从各个方面经历的悲剧性矛盾:与逻辑、伦理和审美意识。 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就更好了! 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不,最好是! 成为——这比什么都重要! 存在是美妙的!
动植物世界的生活充满了残酷、苦难、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它的本质是悲剧,因为它是丑陋的,同时又是美丽的。 大自然的悲剧在于它的冷漠,如果它没有永恒美丽的奇异光芒,如果它没有唤醒灵魂不由自主的认识,它就不是悲剧(就这样吧!——让它……) .
然而,如果我们上升到被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对自由人的命运、对历史的命运,那么在这里,生命的本质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生动地揭示为一场悲剧. 佛陀看到了它,苏格拉底经历了它,基督把它提升到了神人的终极高度。 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命运中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人子的命运——不承认他是最美丽的,在“律法主义”的指责中,在法利赛人的敌意中,在门徒的背叛中,在生命的十字架之路。 历史是悲惨的——无论是在个人传记中还是在国家传记中。
如果还有其他更高的超人程度,正如所有宗教所预设的那样,天使、半神人、泰坦和英雄的世界,即使在那里,他们生命中最高的成就也是悲剧,这从最美丽的人的悲惨命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的天使。 悲剧是主要的历史范畴,同时也是生命中最充实和丰富的最高范畴。 因为历史必须是所有生命的历史,包括它的所有方面和全部。 如果说每一个“我”的生命,每一个精神生命的生命,都是必然与自由的奇异结合,正如我们亲身经历的那样,那么历史的悲剧必然是自由的命运,或者命运力量下的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在命运的力量之下,只有悲剧英雄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命运。 生物的、因果的必然性不是命运。
所以,我们不需要证明生活是一场悲剧——每个人都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 即使是幸福的经历也不能消除悲剧,因为它是悲剧的一个时刻(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至上妙乐的灭亡是悲惨的,历史,人类的命运,没有永恒的幸福。 也许他们会反对我们说,日常生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滑稽,而国家历史的每一步都揭示了“命运的讽刺”。 没错。 但关键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剧的时刻。 他在每一场悲剧中都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拥抱生命的充实; 毕竟,悲剧和喜剧的本质,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皮洛士》中也暗示的那样,是相同的。 命运的讽刺往往是悲剧性的,民族的历史是一出悲喜剧。
然而,有必要证明这个说法,有必要评估它的所有深度和严重性,因为人类在其重要的部分被以任何方式避免悲剧的愿望所激发,以任何方式向自己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而在历史上顺风顺水,进步,进步,进化,无误地到达最后的人间天堂。 没有悲剧的历史哲学非常广泛和多样。 这里首先是关于人类不断进化和进步的无神论。 孔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完全遵循了自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和提图斯·卢克莱修斯·卡尔以来一直推行的这条路线。 坦率地说,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说,伊壁鸠鲁主义的驱动神经是摧毁生活中所有悲剧的愿望,尤其是与另一个世界及其力量相遇的悲剧。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给自足的人性的天真乐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并凭借一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自行发生。
黑格尔关于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的公式,也是一种非悲剧性历史哲学的尝试——沿着理性主义和泛神论的一元论道路,将人类及其科学和国家地位视为最高程度的绝对精神,例如哲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无神论的“人类宗教”、费尔巴哈和马克思。 她以同样乐观的理性主义向我们保证,历史上的暴行只是“自由祭坛前的牺牲”,而这里的自由是对所有生命的理性调节的庆祝——这正是一种“自由”马克思也明白这一点。 一切进展顺利,朝着“有意识”和社会安排良好的人类发展。 对历史的非宗教理解的现代形式是多么深刻、更加严肃、更加接近悲剧性的现实,就像我们在斯宾格勒身上看到的那样:万物生长、开花、凋谢,万物趋于日落!
然而,非悲剧历史哲学不仅有无神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称之为非悲剧人类学; 也有一些非悲剧性的神学起源于对神的理解,但在本质上仍然惊人地接近于第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 目的论行动的自然,目的论发展的人类,目的论进步的经济,所有这些没有上帝的天意,或者更准确地说,由假神执行的天意——这一切都被世界和历史上神性的目的论行动所取代。 哲学上的巧合正是在幼稚的理性目的论中:最终的原因也是效率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有什么特别悲惨的事情,最终,在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莱布尼茨原则上采用了斯多葛派的理性主义神学。 天意基本上是理性的——每一个困境和每一个悲剧都被解决到最后。 乍一看,自然界和历史中的许多事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上,天意已经预见到了一切,并将每一种邪恶都变成了实现更大善的手段。 斯多葛派的幼稚理性主义断言,虫子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不要睡太久,老鼠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物品乱七八糟,原则上与莱布尼茨的宏大的普遍理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被迫承认犹大的内疚是一种“有福的内疚”(beata culpa, qui talem redemptorem exiguit)。
事实上,我们不是神学,而是对神进行最可怕的道德指控,根据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原则,在罪恶、眼泪和苦难上建立它的王国。 如果这就是“最好的世界”中的情况,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与伊万卡拉马佐夫一起拒绝所有世界——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 叔本华是对的:试图绕过悲剧将神义论引向最庸俗的乐观主义: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很好! 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道德杂耍,结局是美好的。
罗马天主教理性主义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斯多葛学说的天意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天意学说。 除此之外,还有赎罪的法律理论,将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各各他——转变为人类与上帝之间理性进行并成功结束的过程。 在这里,所有的悲剧都被彻底消除:上帝得到了公正的满足,人类得到了救赎和拯救。
这里对悲剧的破坏主要是通过法律范畴的应用来实现的。 然而,悲剧避开了所有的法律范畴:试着合法地思考奥赛罗或麦克白的事情,你会得到一系列平淡的陈词滥调。 这表明悲剧的范畴比法律的范畴更高、更复杂,因此也是非理性的。 也许悲剧是存在的终极非理性最真实的表现——最大和终极困境的集中和凝结,因为如果不存在这种难以理解的僵局(aporia),那么就其本身而言,就没有真正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悲剧的,在它的困境中,而哲学——在它的极端矛盾中(比如里奇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的感叹:“是的,它是荒谬的,但它又如何,因为它存在”),伦理学也是悲剧的——在无休止的价值观冲突中,在其“pereat mundus, fiat iustitia”[让正义,即使世界灭亡]中,艺术是悲剧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它的顶峰是悲剧,宗教也是悲剧——在它的神秘中tremendum(人落入永生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不断地接近上帝,无限地与上帝分离——被上帝遗弃。 所有生命和整个世界历史的悲剧——普遍的、宗教的、神圣的和上帝-人类的悲剧——在其自身中包含着世界所有僵局、不可理解性和矛盾的集中,作为一个焦点。 这里是问题的问题,冲突点和不可理解的统一点,这里是不相容的对立面的和解点。 全能的上帝把不可抗拒的推开的东西握在他的手中。 这种不相容的和解被体验为惊奇、恐怖、悲剧。 与此同时,他最强烈地感受到上帝之手。 这就是为什么落入活神的手中是可怕的,而这种恐惧是最古老的悲剧体验。
只有在这里,那种奇怪的精神体验才能得到解释,在苦难、僵局和放弃上帝的过程中,最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在这里,在极端的悲剧中,真正的神正论被隐藏起来,因为这是上帝被揭示的地方——在他的天意的不可理解中。
“从我的深处(de profundis)我向你哭泣,主啊!”
Wer nie sein Brot mit Trähnen 作为,
We nie die kummervollen Nächte
Auf seinem Bette weinend sas,
Der kennt euch nicht, ihr himmlsche Mächte!
[2]
约伯的命运清楚地表明,人类与上帝的相遇正是在最深刻的悲剧经历中发生的,正是在这里——在这最后一个为什么? ——人与神面对面,却看不到他的面。 可以说:在神作的地方,凡是人都无法理解的,凡是能理解的,就没有与神相遇的地方——人的计算和预测的内在世界(一种“天意”)。 一个完全解开和合理化的“供应”将不再是神圣的——其合理的权宜之计最明确地表明,这里有人类的意图。 在他们假装的安慰中,约伯的朋友们是理性神义论世界的代表:他们寻求“证明”神,隐藏理性论证的悲剧性不公正的深渊,根据他们的理性在约伯的命运中找到正义和权宜之计。 然而,事实证明,约伯对上帝的指控比他的朋友们发明的理性神义论的“辩护”更真实。 是谁用无意义的话来掩盖天意? 这就是上帝对所有这些“神学”所说的话。
在他的悲惨经历中,约伯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些神学的不公,神自己也证实了这种感觉的绝对正确性。 在明确谴责掩盖天意的人类“神学”之后,他对约伯说了什么? 他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系列天地的问题和奥秘; 他揭示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隐藏自己,作为所有问题的问题; 然后约伯的悲惨绝境变成了神圣奥秘伟大冠冕中的时刻之一。 根据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方法,约伯的故事不能通过这个世界的内在逻各斯来理解和“证明”——它在天堂,在另一个世界有一个序言和一个尾声。 那里发生的事情(上帝对撒旦的命令)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也是人类伦理学无法接受的。 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加深了悲剧和问题主义——在这里,上帝不是由人类的善恶概念来定义的。 毕竟,对于约伯来说,这种超凡脱俗的神学仍然是完全未知的。 上帝没有告诉他关于她的事。
约伯的悲剧,正如我们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确实是各各他的一种,因为各各他是可以超越人子和人子的悲剧的终极表现。 在这里看到理性的权宜之计甚至司法正义,实际上是用毫无意义的语言掩盖了上帝,更糟糕的是——掩盖了善恶的判断(beata culpa!)。 任何理性和神圣的意志都可以渴望理性的权宜之计和正义。 然而,这是最合理和最神圣的意志——神人的意志——所不能要求的。 为此,人类最高的智慧和圣洁,尽管有所有的“神学”,只能说:让这杯从我身边过去吧! 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没有看到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很好? 还是这些话是人性的弱点? 这样的假设将是最肤浅和无关紧要的,它被驳斥:但你的意志会成就。 接受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并不是由于人类理性意识到其合理的权宜之计。 在为杯祈祷中,没有意志的软弱,没有人类知识的局限,而是相反——对人的圣洁意志的绝对真实的判断:我们不能希望神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能接受正义被钉在十字架上,渴望这种罪行,即使完全准备好受苦和自我牺牲。 约伯一直在祈祷:让这杯从我手中过去! 就像基督一样——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意识到他的绝对权利。 我们不应该渴望受苦受辱的公义。
如果我们承认基督里的一个意志(一神论异端)——只有人类的或只有神性的,髑髅地的悲剧就会消失。 悲剧只有在两种意志的肯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人类的和神圣的; 教会最伟大的父亲之一——忏悔者马克西姆——为此而殉道的声明。 如果在这杯离开我的杯子中表达了意志,人子的圣意,那么在你的意志中,而不是我的,父的神圣旨意存在(我与父原为一)。 悲剧的实际困境是,人的意志可以是绝对有价值和圣洁的,即使它与天父的旨意相抵触,也无法实现。 这是约伯的朋友无法理解的。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Vysheslavtsev, B. “Tragic Theodicy” – In: Put, 9, 1928, pp. 13-31(俄文)。
笔记:
[1] Karsavin, L. 圣父和教会教师,巴黎,1927 年,p。 31.
[2] 谁没有为他的面包流泪
谁在他的床边,就像在坟墓边
在不眠之夜他不哭——
他不认识你,哦更高的力量!
(歌德,威廉·迈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