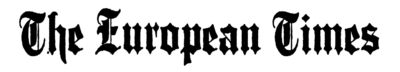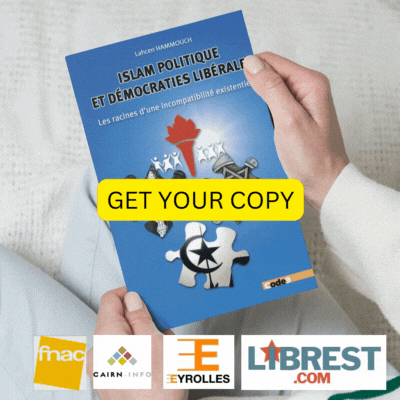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教会由许多社区组成,完全分离和独立,彼此之间没有规范的联系——在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中。 与此同时,基督徒联合教会的意识从未如此强烈,正如当时“联合教会不仅仅是一个想法,而是最真实的事实”。 [1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独立的自治市——就其本身,在它的地方合一中——都有上帝子民合一的活生生的经历。 并且“外部组织的统一并不存在,不是因为它据称与基督教的教会观念相悖,正如新教学者倾向于想象的那样,而是因为实际上存在这样的统一,更深,更窄。 与后来的共融形式——正式的、司法的和大法官的——相比,在教会早期可以区分的共融形式证明了基督徒对单一教会理念的更大渗透”。 [16] 换句话说,教会的合一不是由规范的纽带决定的,而是它们本身代表了这种合一的发展、体现和保存,而这种合一首先是在地方教会的合一中给予的。
所以,地方性和普遍性——这就是教会天主教的双重基础。 独一普世教会不是分裂成独立的部分,也不是某个教会的联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每个成员都与整体的生命一起生活,并在自身中反映其所有的丰满。 因此,地方团结成为教会普遍性的必要条件,是其大公性的有机基础。
4. 教会制度的发展
然而,如果地方性原则是教会结构的首要和基本规范,是从教会的本质有机地产生的,那么在历史上,这一原则的体现方式不同——取决于教会生活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
这一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将地方教会统一为更大的教会区域,并同时建立高级和初级教会的等级制度。 最初,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之后在这些最初的中心周围逐渐出现了新的社区,这些社区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与各自的母教会的联系,他们从中获得了等级制度,即“信仰规则”他们成立的时间。 和礼仪传统。 因此,即使在迫害时代,自然教会协会或地区已经形成,高级教会的主教获得了大都会的称号。 The metropolitan ordained the newly elected bishops in his area, twice a year presided over regional episcopal councils and was the appellate authority in cases between individual bishops or in complaints against bishops. 反过来,大都市围绕着最古老或最都市的大教堂——罗马、安提阿等地进行分组,其主教后来被称为族长。 在转换小鬼的时候。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来说,这种自然发展的教会组织结构几乎得到普遍肯定,并在第一届普世大公会议(325)上得到批准。 [17]
当然,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和解对教会的生活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从此教会的外部命运开始越来越多地由它与国家的联合来决定。 自从罗马帝国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的所有臣民都成为了教会的成员,教会也相当一致地开始将其结构与帝国的行政结构相协调。 “教会堂区的秩序应该遵循国家和公民的分配”——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教规所说的(第四届普世理事会,17;特鲁尔理事会,38)。 [18] 与此同时,教会在五大宗主教区的最终分布也得到了确认,其中——由于上述原因——一些主教教堂的重要性与其各自的重要性有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城市。 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重要性和权力的迅速增长,他已经在第二次大公会议(从 381 年)上接受了——作为“国王和 Synclitus 城市的主教”(规则 3 )[19] – 仅次于旧罗马的主教。 [20]
我们谈论这种演变,因为其中清楚地概述了教会结构发展的有机法则。 一方面,教会总是“追随”历史,即它有意识地、系统地调整其结构以适应它所生活的世界的形式。 然而,在这种改编中,它并没有改变那些代表其本质的、不能依赖于外部历史条件的基础。 无论教会的分组制度、彼此的资历、理事会机构的行动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地方原则都保持不变——这是所有不同形式的教会组织成长的根源。 大公会议和地方议会的规范活动总是旨在维护这一原则——“教会不应混合”(第二次大公会议,规则 2)。 [21] 在这里,我们指的是禁止两个主教在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教规,规范神职人员从一个教区转移到另一个教区的教规,教规规定“不得执行圣职[在任何教会等级制度中”(注trans. .)],除非被任命为 [某些 (note trans.)] 城镇或乡村教会”[22] 等(参见,例如,第四届普世理事会,规则 6、10、17;特鲁利理事会,20 ; Antioch Council, 9, 12, 22; Serdic Council, 12)。 在适当的历史和教会背景下理解,所有这些教规实际上都保留了教会生活的相同基本事实——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地方,在一位主教的仁慈权威下团结起来,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有机的统一,展示并体现教会的天主教和普遍本质。
因此,与这一发展有关,我们只能重复已经引用过的神父的话。 N. Afanasiev:“教会生活不能采取任意形式,而只能是那些符合教会本质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表达这种本质的形式。”
5. 地方性、普遍性、国家性
注意到教会组织发展的这一基本原则的不变性和“有机性”特征之后,现在有必要追溯那个在后拜占庭时代逐渐进入教会生活并且已经相当成熟的新因素的作用。密切地把我们引向我们现代的困难。 这个因素是国家因素。
罗马帝国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性的、超国家的帝国,甚至称自己为“宇宙”(ecumena)。 成为一名基督徒,即接受基督教作为她的信仰,她继续看到她自己的宗教使命和目的是在统一的基督教王国中统一所有民族,在世俗方面对应于所有人在一个普世教会中的统一。 [23] 这种信念也被教会的代表所认同(尽管他们从未“教条化”)。 因此,在当时的拜占庭教会著作中,常常指出人类在一个普遍的国家和一个真正的宗教中统一的同时是天意的巧合。
但我们是否必须提醒,这个统一的基督教王国的梦想注定不会实现,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越来越失去其普遍性? 起初,野蛮人的入侵将西方与它隔绝开来,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不间断地——直到它最终崩溃的那一刻——从北方和东方蚕食它。 在 9 至 10 世纪,拜占庭成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希腊国家,四周被新兴的“野蛮”国家所包围。 反过来,后者与拜占庭交战,因此与拜占庭进行了最密切的接触,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拜占庭的宗教和文化影响,并接受了基督教。 在这里,教会民族主义的问题第一次被特别尖锐地提出。
现在,与迫害时代基督教传播的初始阶段相比,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国家,已经接受了它,并因个人皈依而受洗。 因此,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实行基督教,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民族和政治特征。 这就是 9 世纪保加利亚的皈依,10 世纪俄罗斯的皈依。 对于圣亲王鲍里斯和圣弗拉基米尔来说,本国人民的皈依不仅是他们通过真正信仰之光的启蒙,也是走向民族国家自决和自我肯定的途径。
然而,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年轻的东正教民族从拜占庭看到的宗教政治概念及其对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国家的理想再次与拜占庭的单一东正教王国的概念发生了冲突——这一理想尽管具有历史意义。失败,继续主宰拜占庭人的思想和心灵。 在拜占庭思想中,新民族的皈依自然意味着他们被引入了单一的帝国宗教国家有机体,他们通常从属于普遍的东正教王国。 但实际上,同一个王国早已失去其真正的普遍性和超国家性,对于新皈依的人民来说,拜占庭的意识形态经常变成希腊的教会政治帝国主义。 那时,“在希腊教会中,早期基督教普遍在爱中合一的悲怆已经基本熄灭。 很多时候,希腊民族的悲怆代替了它……在拜占庭本身,曾经强大的语言和弦,如此美妙地呈现在锡安山上,作为所有民族中基督教福音的象征和标志,几乎不再响起.[24] 因此,这些民族主义之间开始了一场斗争,由于其宗教性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教会生活。 年轻的东正教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获得教会自治——作为其教会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他们争取自治作为一条红线从那时到今天贯穿东正教世界的整个历史。 [25] ]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将立即非常明确地声明,基督教的这个国家时刻本身远非一件邪恶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许多基督教国家取代了一个基督教王国,这与小鬼皈依基督教一样是历史事实。 康斯坦丁。 由于它不绝对化存在于它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任何形式的历史存在,教会可以同样地使其生活适应希腊罗马的普遍帝国概念和国家形式的国家形式。 教会一直既彻底地“在这个世界上”,又同样彻底地“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的本质,她的生命,不依赖于这个世界的形式。 再者,正如帝国与基督教历经三个世纪的冲突而和解,在基督教国家理想和基督教文化面前结出了伟大和神圣的果实,对实现目的和意义的基督教民族的教育也是如此。他们在为基督教真理服务和将他的国家礼物奉献给上帝的国家存在中,教会的永不褪色的荣耀永远存在。 这就是神圣罗斯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的理想——这种理想与培育它的东正教密不可分。 教会曾经以“普遍”的方式祝福了帝国,因此祝福并圣化了这个同样真理的国家事工。
但是,在基督教中对民族的所有积极价值给予应有的肯定,我们也不能陷入历史的理想化。 看到光,我们不能对阴影闭上眼睛。 教会在这个世界的道路——在尘世的历史中——从来都不是田园诗,需要教会意识的不懈壮举和张力。 没有任何公式本身是有益的——普世帝国、神圣罗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交响乐”都不是——这些形式中的每一个都必须不断地填充理论正确性和活生生的正义。 因为正如拜占庭式的教会与国家之间“交响乐”的理想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国家对教会的简单从属,所以在这里,在这条新的国家道路的条件下——带着它的阴暗面——有教会在国民面前的从属地位,比教会对国民的启蒙更重要。 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价值等级的潜意识变化——当人们不再为基督教真理服务并以此衡量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时,反之亦然——基督教本身和教会本身开始被衡量并从他们在人民、祖国、国家等面前的“优点”的角度来评估。如今,唉,对许多人来说,教会存在的权利应该通过其国家和国家的优点来证明是很自然的,通过它的“功利”价值。 谈到神圣的俄罗斯,他们常常忘记,对于背负这一理想的古代俄罗斯来说,民族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服务于基督教真理,保护它免受“异教徒”的侵害,保护它真正的信仰,在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这种信仰。换句话说,这种宗教-民族理想的真正公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位伟大的俄罗斯教皇所说的“教会拥有一直和它的人在一起。” 然而,对于古代俄罗斯的思想家和思想家来说,人民的价值恰恰在于人民始终与教会同在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民族的领域,血脉、元素和未开化的感觉和情绪的声音如此强烈,所以有必要“站岗”并辨别精神——它们是否来自上帝。
6. 普遍意识的解体
同时,虽然在教会的历史上,新民族的“教会”写下了许多光明和圣洁的篇章,但不可否认,与它同时在正教中普遍意识的瓦解已经开始. 而这恰恰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教会组织的问题不仅在教会中提出,而且在政治和国家层面也被提出。 每个民族国家的主要目标已成为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自治,这被理解为特定的民族教会独立于古老的东方中心,尤其是君士坦丁堡。 我们将重复一遍:这里的重点不是责备或捍卫任何人。 不可否认,这一悲惨过程的基础首先是拜占庭普遍主义退化为希腊民族主义。 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将自治和独立的语义等同起来是当时教会中出现的一种新精神的典型现象,它证明了教会意识已经开始由国家-国民从内部决定,而不是它本身定义和启发这个国家-国民。 民族和政治范畴被无意识地转移到教会结构中,而关于教会结构的形式不是由这些范畴决定的,而是由教会作为一个神人有机体的本质决定的意识已经减弱。
(未完待续)
*“教会和教会结构。 关于书籍保护。 苏联和国外最高教会当局的波兰规范立场” – 在:Shmema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47-1983), M.: “Русский пут” 2009, pp. 314-336; 该文本最初发表于:1949 年,巴黎,西欧东正教俄罗斯主教区的教堂公报。
笔记:
[15] Troitskyi, V. Cit。 同上,第52.
[16]同上,p。 58。
[17] 这种演变的详细说明:Bolotov, VV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3, St. Petersburg。 1913 年,第 210 页以下; Gidulyanov,P. 基督教前三个世纪的大都会,M. 1905; Myshtsin, V. 前两个世纪基督教会的结构,圣彼得堡。 1909; Suvorov, N. Church Law Course, 1, 1889, p. 34 岁以下。
[18] 见:圣正教会的规则及其解释,1,p。 591; 2,第195(译注)。
[19] 从字面上看,该规则的文本如下:“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罗马主教之后享有优先荣誉,因为这座城市是一个新罗马”(圣正教会规则及其解释,1,p . 386). 作者引用的文字来自第四届大公会议规则 28 (451),它确认和补充了第二届大公会议规则 3 的含义:同上,第 633-634 页(译注) .
[20] 关于这个问题:Bolotov, V. Cit。 同上。 cit., pp. 223 ff. 和巴尔索夫,T. 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和圣彼得堡俄罗斯教会的自我权力。 1878 年。
[21] 圣正教会的规则及其解释,1,p。 378(译注)。
[22] 同上,p。 535(译注)。
[23] 关于这个理想及其来源,请参见:Kartashev, A. “Судьбы Святий Руси” – 在: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ысл, Труды Правосл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 П1ариже, 1928, П140ариже, 5, П1948ариже, 130,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ысл, Труды Правословного 147 英尺。 另见我的作品“Судьбы бизантийской теократии” – 同上,XNUMX 年 XNUMX 月,第 XNUMX-XNUMX 页。
这篇文章由神父翻译。 Alexander in:基督教与文化,4 年 2009 月,第 52-70 页(注译)。
[24] Cyprian (Kern), 阿奇姆。 Antonin Kapustin 神父(大主教和俄罗斯驻耶路撒冷精神传教团的负责人),贝尔格莱德,1934 年,第76.
[25] 关于这场斗争的历史:Golubinskii, E. Правословних Церквей Болгарской, Ребской и Руменской, M., 1871 年历史概要; 列别杰夫,美联社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东部教会历史,1-2,谢尔吉耶夫镇,1896 年; N. Radožić “圣。 Savva and autocephaly Tserkvei Serbskoi i Bolgarskoi”——载于:Glasnik Serbskoi Akademii Nauk,1939 年,第 175-258 页; 巴尔索夫,T. Cit。 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