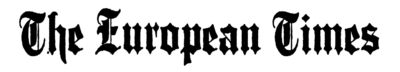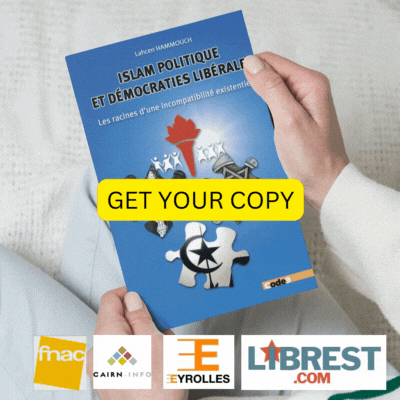1月XNUMX日,示威者在香港抗议国家安全法时游行。(CNS/路透社/Tyrone Siu)
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于 14 月 XNUMX 日证实,罗马教廷打算与中国政府续签为期两年的关于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任命天主教主教的协议。
帕罗林是 与记者交谈 在已故红衣主教 Achille Silvestrini 的纪念活动的边缘,他是梵蒂冈在冷战后期东方政治时期战略的建筑师,或与东欧共产主义当局进行对话。
2018 年 XNUMX 月梵中协议是教皇方济各任教皇和帕罗林担任国务卿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成功。 其更新的双边会谈是 进行; 鉴于中美之间存在新冷战的危险,他们的反响和引发的兴趣远高于其他涉及罗马教廷的秘密外交会谈。
当然,在美国教会的某些地方,续签协议的前景已经引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天主教的支持者的恐慌。
其中最著名的批评家是乔治·威格尔,他写道 31 月 XNUMX 日的专栏文章 《华盛顿邮报》——这只是他过去几年反对教廷对中国开放的系列文章中的最新一篇。 这篇文章以它自己的方式很重要,因为它展示了指导魏格尔的错误历史和神学假设。
第一个错误假设是,梵中协议的历史先例东方政治是失败的。 Weigel 写道:“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欧和东欧失败的梵蒂冈东方政治只成功地使当地天主教社区失去了能力和士气,而梵蒂冈本身则被共产主义情报机构深深渗透。”
这是韦格尔经常重复出现的主题,它在美国以及最近在东欧的保守倾向天主教知识界变得很普遍——冷战后世界的拒绝现在受到反自由主义者的青睐。大陆的一部分。 (Anne Applebaum 最近在她的书中描述了这一点 民主的黄昏:威权主义的诱人诱惑.)

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彼得罗·帕罗林于 3 月 XNUMX 日在梵蒂冈(CNS/Paul Haring)
魏格尔对近期教会历史的意识形态解释没有认识到东方政治的成功。 例如,共产党当局允许波兰红衣主教参加 1978 年的两次会议,第二次选举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为约翰·保罗二世。
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是另一个 主要成就 梵蒂冈东方政治。 它们帮助为罗马教廷的外交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有时被视为教皇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赫尔辛基协定》原则 VII 申明“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 宗教 或信仰”,并指出“参与国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意义,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和平、正义和福祉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这些协议对保护东欧的异议形式很有用,它们为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魏格尔认为梵蒂冈东方政治的一个重大好处是失败的。
第二个错误假设是,方济各和帕罗林的对华政策可以与梵蒂冈在 20 世纪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其他外交开放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进行一系列区分。
当代中国政权更多的是关于世界霸权,而不是共产主义:它更多的是关于中国重新成为其前王朝、帝国自我(就像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一样)的想法,而不是关于毛主席的想法。
Ostpolitik 的目标是天主教会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摇篮欧洲的生存,而梵蒂冈-中国协议发生在一个新的全球情景中,基督教在大多数国家是宗教、文化和政治世界中的少数群体差异。
广告
广告
这不是关于欧洲和西半球,而是关于全球世界的全球天主教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Wojtyla 对二战后的波兰进行了完全误导性的比较。 一个更恰当的比较是,例如,今天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天主教会的地位,或者更好的是,17 世纪和 18 世纪在中国的地位。
将两者进行类比是很有趣的 宗教 和经济。 正如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西斯科·西西 最近写 《亚洲时报》:“以前的冷战很容易。 问题是生意还是没有生意:西方及其阵线是亲商的。 苏联及其盟国认为商业是万恶之母。 政治紧随其后。 […] 目前的冷战更加微妙,它与生意或没有生意无关。 这是关于什么样的生意和什么样的政治。”
宗教也是如此。 习近平的中国与二战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官方无神论意识形态无关。 在今天习近平的中国,宗教可以蓬勃发展,但前提是它不挑战政治,帮助政治。
第三个错误假设与我们所说的梵蒂冈和教皇权有关。 威格尔写道:“梵蒂冈在 21 世纪的全球政治中拥有的唯一权力是直截了当捍卫所有人人权的道德权威。”
这只是部分正确。 本月,天主教徒纪念了 150 年 1870 月这一戏剧性的 XNUMX 周年:在梵蒂冈第一届理事会上宣布教皇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意大利人占领罗马,教皇国解体,以及理事会最终中断。
自 1870 年以来,罗马教廷吸取的惨痛教训之一是,教皇外交必须更多地依赖教皇道德权威的行使,而不是通常的有形国家权力工具。

佘山圣母小教堂,中国上海基督徒的帮助(CNS/Nancy Wiechec)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秩序破坏的未知领域以及这种破坏对当今全球宗教格局造成的后果,使罗马教廷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独特性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教皇的道德权威与其他教会不同,还因为某些国家权力工具是圣座活动的关键方面。 (想想罗马教廷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派驻罗马教廷的外交使团,它作为联合国常驻观察员的地位,以及它签署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作为中国专家米歇尔·尚本 写于 2018 年 XNUMX 月,在宣布梵中协议之前:“当记者和其他活动人士将[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这次相遇仅仅视为道德问题时,他们确实贬低了这种对话的法律方面。 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他们阴险地否认了圣座的权利,因此也否认了圣父本人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权利。 在他们眼中,教皇应该只是一个道德领袖,告诉世界什么是“善”。 这种做法是有很大问题的,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人应该仔细质疑它。”
2014 年我曾在香港任教过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仍然有朋友。 看到那个城市和那里的教堂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知道中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
但正如我在中国报纸《环球时报》上所写 二月2018,必须考虑的是圣座国际活动的长期历史框架及其外交活动的牧灵目标。
在当今全球成为天主教会意味着艰难的选择。 圣座和教皇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负责任的行动意味着没有简单或简单的解决方案。
[Massimo Faggioli 是维拉诺瓦大学的神学和宗教研究教授。 他最近的一本书是 教皇弗朗西斯的阈限教皇权:走向全球天主教 (奥比斯)。 在推特上关注他: @MassimoFaggio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