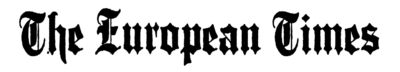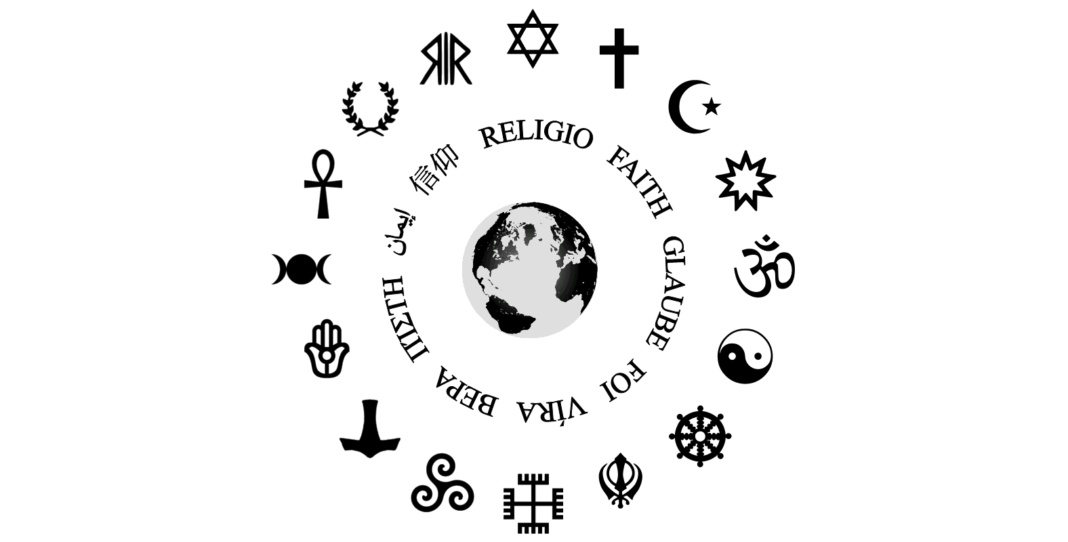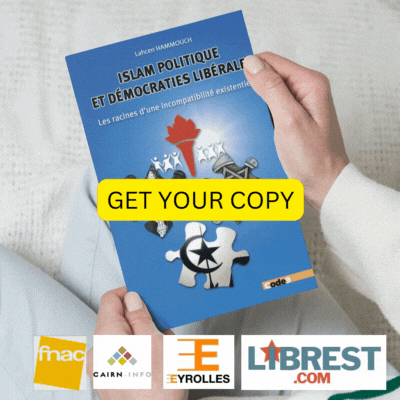摘自大卫·B·哈特 (David B. Hart) 的《无神论妄想》一书
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一些伟大的早期理论家相信魔法,因此往往倾向于向那些将其用于恶意目的的人提出迫害。 罗德尼·史塔克 (Rodney Stark) 并没有夸大其词,他说“对撒旦巫术现实的第一个严重反对意见来自西班牙的审判官,而不是来自学者。” 我们甚至可以争辩说,对魔法的兴趣(尽管不是对它的恶意变种)一直是现代科学思想演变的主要成分之一。 毫无疑问,Corpus Hermeticum [13]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发现——这本宏伟的晚期古董选集汇集了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炼金术、魔法、占星术和 宗教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弗朗西斯·培根 (1561-1626),他为定义现代科学方法的内在合理性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如此积极地倡导人类认识和征服物质世界的“使命”,至少是强调的延续. ,赫尔墨斯主义的复兴将人类的神圣权利置于物质创造的较低层次之上,以及分解元素性质的炼金术传统,以便揭示其最深的秘密。 罗伯特·博伊尔(1627-1691),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研究气压和真空的先驱,是炼金术的学生,对现实深信不疑女巫和消除它们的必要性。 约瑟夫·格伦维尔(Joseph Glenville,1636-1680 年)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也是他的实验方法的主要辩护者,他认为巫术的真实性是可以通过科学证明的。 [14] 甚至牛顿在他的炼金术上投入的精力也远远多于他的物理理论。
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兴起和早期现代性对巫术的痴迷不仅是西方社会的当代潮流,而且是一种新的后基督教人类统治世界意识展开的两个密切相关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离谱的。 毕竟,魔术本质上只是一种唯物主义:如果它诉诸可见领域之外的任何因素,这些因素都不是超自然的——在神学意义上,“超越”。 关于它们,最多可以说的是它们只是非凡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物质宇宙中更难以捉摸、更强大的方面。 赫尔墨斯魔法和现代科学(至少以最培根的形式)都同样关注物质秩序中的隐藏力量——完全没有人格和道德中立的力量,我们可以学会操纵。 我们的目标既是高尚的,也是卑鄙的。 换言之,两者都参与了对物质宇宙的统治,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从属,以及人类力量的不断增强。 因此,人们不能真正谈论科学对魔法的任何迟来的胜利,而只是自然地取代第一个中的最后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完成魔法的能力只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现代,“魔法”和“科学”只能追溯地加以区分——根据它们各自的有效性程度。 然而,两者之间从未有过对立:形而上学、道德上和概念上,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连续体。
至于 15 世纪和 1970 世纪对恶意魔法和撒旦教的普遍恐惧,当关于恶魔、附身、邪灵和夜魔的论文以它们的印记迅速传播时,[XNUMX] 很容易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任何那些令人讨厌和莫名其妙的流行热情形式,例如不明飞行物、雪人、尼斯湖水怪或百慕大三角的魅力,这将只是 XNUMX 年代特定白痴的主要内容,只要他们后果并没有那么悲惨和持久。 一个更好的类比是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社会的恐慌。 由于狄俄尼索斯或巴克斯的崇拜迁移到意大利,当时有传言说黑暗时代的狂欢,妇女毒害丈夫,贵族家庭的孩子参与仪式谋杀。 Bacchanalia 随后被取缔,对他们的指控通过奖励和酷刑逼供,并下令处决数千人。 然而,抛开所有的类比,现代早期对撒旦教徒和女巫的迷恋一定是在西方基督教秩序的那些世纪兴起的,这不足为奇。 欧洲 正在慢慢瓦解,教会对人民行为的权威已经削弱,旧信仰不再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来对抗自然、历史和命运的黑暗和无名力量。 正如基督教对超然的上帝创造者的信仰曾经剥夺了魔法以任何方式在宗教或哲学上严肃地出现,诉诸单纯的迷信和简单的工艺,同样,基督教欧洲的分裂可能鼓励了某种魔法思维来重新-在这个悲惨而混乱的时代的恐惧中出现并被忽视。 然而,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充分“解释”现代早期的非同寻常的暴行和狂热的所有表现,尚无定论。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证明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与暴力共谋,或者因为它实际存在的日益尖锐和偏执狂而为之辩护。 所有强大的机构都害怕权力的衰落。 它也无意否认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性是一个以铲除异端为标志的时期,在小鬼时代是无与伦比的。 查士丁尼一世以后。
例如,很难忽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它在西方文化的集体噩梦中占据如此特殊的位置。 但是,即使在这里也需要考虑某些事实。 一方面,四十年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对宗教裁判所的许多传统概念只是草率的夸大和耸人听闻的捏造; 在其存在的三个多世纪里,宗教裁判所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傲慢和强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正如任何被指控犯有巫术的西班牙人有理由理解的那样,它的行为就像对世俗法庭的残酷行为的有益制止。 然而,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宗教裁判所——在原则上总是,而且在其行动中经常——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机构,它在其活动的头二十年里 西班牙 尤其残忍,而且酷刑或火刑柱的相对罕见并不会使这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那么可怕。 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原则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皇家政策和服务的问题,由国家支配。
诚然,早期宗教裁判所的创始人是教皇西斯图斯四世 (1414-1484),但他是在费尔南多国王 (1452-1516) 和伊莎贝拉女王 (1451-1504) 的压力下这样做的,后者在穆斯林占领安达卢西亚几个世纪后, – 渴望任何在他们看来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加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权力的工具。 然而,早期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性和其圈子的腐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快西斯图斯四世就试图干预其行动。 在 1482 年 1483 月的教皇诏书中,他毫不妥协地谴责和谴责宗教裁判所对无辜生命的破坏和财产的没收(当然,他原则上并不反对处决真正的异端)。 然而,费尔南多实际上拒绝承认这头公牛,并在 1420 年迫使西斯图斯四世放弃对宗教裁判所的控制权让给西班牙王位,并同意由民政当局任命大调查官。 第一个获得这个头衔的人是臭名昭著的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homas de Torquemada,1498-1431 年),他是一位极其严格和不妥协的牧师,尤其是在皈依者方面:那些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的人。 他怀疑这与他们旧信仰的教义有关。 到他最终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503-1484)约束时,他已经负责将大量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并且很可能对大约两千名“异教徒”的处决负责。 然而,即使在西斯图斯四世将他的权力移交给宗教裁判所之后,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宗教裁判所的极端抵抗。 例如,在 1432 年,他在被拒绝进入宗教裁判所后支持了特鲁埃尔市,次年费尔南多以武力镇压了一场起义。 西斯图斯四世和他的继任者英诺森特八世(1492-1491)继续零星地要求宗教裁判所给予更大的宽大处理,并试图在吉祥的时候干预皈依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宗教裁判所经常被卷入令人作呕的“纯血统”(limpieza de sangre)国家政策,其中没有人是安全的——甚至是僧侣、神父或大主教。 西班牙本身对西班牙激进主义有一些抵抗,没有一种抵抗形式像耶稣会教团的创始人伊格内修斯·洛约拉(Ignatius Loyola,1556-16 年)那样值得尊敬和毫不妥协。 然而,种族主义骚扰的缓解,无论多么微弱或不频繁,通常都是由教皇干预提供的。 [XNUMX]
我们如何理解所有这些故事? 我们是否应该从他们那里得出结论,宗教本身会带来死亡,或者不容忍与“极端信仰”有着内在联系? 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故事视为基督教固有的残忍的证据? 当然,西方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至少从表面上看——对寻求定罪证据的反基督教论战者更具吸引力。 然而,对我来说很明显,我们需要学习的真正教训恰恰相反,这个教训是关于国家固有的暴力和机构教会曾经允许自己卷入世俗政治的悲剧。 它曾经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国家或帝国统一的责任。 认为崇拜神灵和对帝国的忠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这对于异教的罗马社会来说是完全自然的,就像罗马法院建立特别的宗教裁判所并将无神论者 [17] 作为叛徒处决一样是自然的。 然而,当 385 年罗马皇帝(或实际上是此类 [18] 的觊觎者)执行 Ep。 普里西拉在西班牙为异端,著名的基督徒,如圣。 土耳其的马丁和圣。 米兰的安布罗斯表示抗议,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异教价值观的庆祝和一种特定的异教暴行,没有一位教父鼓励或批准这种措施。 . 事实上,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坚持异端的唯一惩罚就是从圣体圣餐中逐出教会。 然而,在 XNUMX 和 XNUMX 世纪,在教会与世俗权力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的时代,当教皇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而神圣罗马帝国对旧的帝国秩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当新的宗教运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言不讳时颠覆性的。 对于教会和世俗的权力,社会的支柱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动摇过,混乱似乎即将再次来临,那么整个西欧的异端再次成为重罪。 然而,为了纪念罗马天主教会,应该指出它不是这方面的领导者:例如,在 1051 年,一群天主教徒(或“摩尼教”)被经常被围困的圣徒下令绞死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三世(1017-1056),他不得不承受列日主教的责备。 然而,由于她永远的耻辱,教会放弃了这种方法。 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 (1194-1250) 颁布法律,命令所有异端向世俗权力投降,并在火刑柱上焚烧时,机构教会对此表示同意,但没有任何明显的良心不安迹象。
基督教的悠久历史在道德、知识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丰富成就,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皈依新信仰,其中许多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这个故事也是福音改变和塑造社会的能力与国家吸收任何有用机构的能力之间不断斗争的故事。 然而,如果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西方基督教中的不公正和暴力是基督教信仰固有的某种东西的自然后果,如果世俗国家的出现确实将西方人类从宗教不容忍的统治中拯救出来,那么,回顾西欧历史的进程,我们将不得不发现,它必须是一个连续的,尽管是扭曲的弧线:罗马帝国秩序的黄金时代的衰落,当时宗教暴力被国家的谨慎之手,长期的狂热、残酷、迫害和宗教竞争,然后,在教会逐渐被征服之后,从“信仰时代”的可怕残酷中缓慢回归——一个进步的、更理性、更人道、更少暴力的社会结构。 然而,这正是我们找不到的。 相反,我们注意到暴力与国家声称的主权程度成正比,而且每当中世纪教会在世俗权力的道德领域放弃权威时,不公正和残忍就会盛行。 我们还注意到,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尽管存在着所有的剥夺、不公正和剥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它所继承的帝国文化更加公正、慷慨和(基本上)和平,而且更加和平甚至更加慷慨(如与早期现代时期民族国家的胜利所创造的社会相比,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我不只是在谈论所谓启蒙运动前夕的早期现代性“过渡”时期的暴力。 纯粹从政治上看,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从一个民族主义斗争时代的过渡,在这个时代,国家仍然认为有必要利用宗教机构作为其权力的工具,进入另一个更大的时代。 民族主义斗争,当宗教理由已经过时,因为国家本身已成为一种邪教,其权力成为单一的道德。
笔记:
[12] 斯塔克,R. Op. 同上,第221.
[13] Corpus Hermeticum(或简称 Hermeticum)中的文本归因于融合神 Hermes Trismegistus,并写于埃及古希腊的第二或第三个基督教世纪。
[14] 见:Burton, D., D. Grandy。 魔法、神秘与科学:西方文明中的神秘学,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4 年,p。 180-181。
[15] 在塞缪尔·德·卡西尼、伯纳德·迪·科莫、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马丁·达勒、西尔维斯特罗·马佐里尼、巴托洛梅奥·迪·斯皮纳、让·博丁、勒内·班诺伊斯特、阿方索·德·卡斯特罗、彼得·宾斯菲尔德、弗朗茨的所有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提及阿格里科拉和尼古拉斯雷米。 有关这些作者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Brouette, E.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Satinism。 – 在:撒旦,伦敦:Sheed & Ward,1951,p。 315-317。
[16] 见:Kamen, H.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ical Revi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54、73。
[17] 在这种情况下,“无神论者”是指那些不崇拜异教神祇的人,在迫害期间,这种指责最常针对基督徒。
[18] 我们谈论的是弗拉维乌斯·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奥古斯都——在 383-388 年间篡夺了英国、高卢和西班牙的帝国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