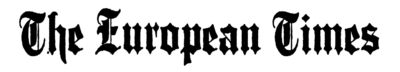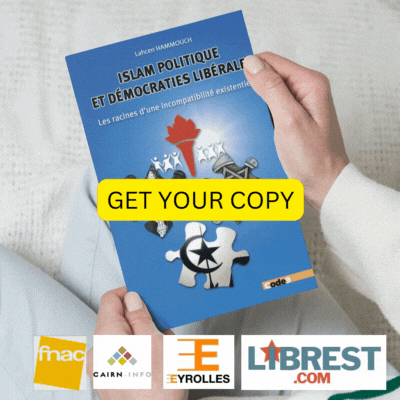富拉尼人、腐败和新游牧主义之间的关系,即富裕的城市居民购买大量牛来隐藏不义之财。
特奥多·德切夫
本分析的前两部分题为“萨赫勒地区——冲突、政变和移民炸弹”和“西非的富拉尼和圣战主义”,讨论了西方恐怖活动的兴起 非洲 无法结束伊斯兰激进分子针对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和尼日利亚政府军发动的游击战。 会议还讨论了中非共和国持续内战的问题。
重要结论之一是,冲突的加剧充满了“移民炸弹”的高风险,这将导致整个欧盟南部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移民压力。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有可能操纵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的冲突强度。 莫斯科将手放在潜在移民爆炸的“柜台”上,很容易对那些通常已被视为敌对的欧盟国家施加诱导性移民压力。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富拉尼人发挥了特殊作用。富拉尼人是一个半游牧民族,是迁徙牲畜饲养者,居住在从几内亚湾到红海的地带,根据各种数据,人口数量为 30 至 35 万。 。 作为历史上在伊斯兰教向非洲尤其是西非的渗透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富拉尼人对伊斯兰激进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尽管他们自称伊斯兰教苏菲派,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伊斯兰教派。宽容,也是最神秘的。
不幸的是,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不仅仅是宗教对立。 冲突不仅是种族宗教冲突。 它是社会、民族、宗教的,近年来,通过腐败积累的财富转化为牲畜所有权的影响——所谓的“新牧业主义”——已经开始发挥额外的强大影响。 这种现象是尼日利亚的独特特征,也是本分析第三部分的主题。
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
尼日利亚是西非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 190 亿居民,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一样,其特点是存在着一种二分法:南方人口主要为约鲁巴基督徒,北方人口主要为穆斯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富拉尼人,他们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迁徙动物饲养者。 总体而言,该国 53% 是穆斯林,47% 是基督徒。
尼日利亚的“中央地带”,从东到西横贯全国,特别包括卡杜纳州(阿布贾北部)、布努埃高原州(阿布贾东部)和塔拉巴州(阿布贾东南部),是尼日利亚和尼日利亚之间的交汇点。这两个世界是农民之间永无止境的仇杀循环中频繁发生的事件的场景,农民通常是基督徒(他们指责富拉尼牧民允许他们的牛群破坏他们的农作物)和游牧富拉尼牧民(他们抱怨牛被盗窃和不断增加的设施)传统上可通往动物迁徙路线的地区的农场)。
近年来,这些冲突愈演愈烈,富拉尼人也寻求扩大其畜群向南方迁徙和放牧的路线,北方草原遭受日益严重的干旱,而南方农民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人口增长的动态,寻求在更北的地方建立农场。
2019 年之后,这种对立在两个社区之间的身份和宗教信仰方向上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变得不可调和并受不同的法律体系管辖,特别是自 2000 年在北部 1960 个州重新引入伊斯兰法 (Sharia) 以来。 (伊斯兰法一直有效到 XNUMX 年,之后随着尼日利亚的独立而被废除)。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富拉尼人希望将他们“伊斯兰化”——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
这种观点的助长是,主要针对基督徒的博科圣地试图利用富拉尼人使用的武装民兵来对付他们的对手,而且事实上,其中一些武装分子已经加入了伊斯兰组织的行列。 基督徒相信富拉尼人(以及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豪萨人)是博科圣地的核心力量。 鉴于许多富拉尼民兵仍然保持自治,这种看法有些夸张。 但事实是,到了2019年,对抗已经恶化。 [38]
因此,23 年 2018 月 200 日,在一个主要由基督徒(卢热族)居住的村庄里,一场归因于富拉尼人的袭击导致重大人员伤亡——XNUMX 人死亡。
富拉尼人、最大的富拉尼文化协会塔比塔普拉库国际前领导人穆罕默杜·布哈里当选共和国总统无助于缓解紧张局势。 总统经常被指控暗中支持他的富拉尼父母,而不是指示安全部队打击他们的犯罪活动。
尼日利亚富拉尼人的处境也表明了迁徙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关系的一些新趋势。 在 2020 年的某个时候,研究人员已经无可争议地确定,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和冲突数量明显增加。 [5]
新游牧民族和富拉尼族
人们援引气候变化、沙漠扩大、地区冲突、人口增长、人口贩运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和事实来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问题是,这些问题都不能充分解释一些牧民和定居农民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急剧增加的原因。 [5]
奥莱因卡·阿贾拉(Olayinka Ajala)特别关注了这个问题,他研究了多年来牲畜所有权的变化,他称之为“新牧区主义”,作为这些群体之间武装冲突数量增加的可能解释。
新田园主义一词最早由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马修·路易扎(Matthew Luizza)使用,用来描述富裕的城市精英对田园(迁徙)畜牧业传统形式的颠覆,他们冒险投资并从事这种畜牧业,以掩盖被盗的畜牧业。或不义之财。 (Luizza、Matthew,《非洲牧民已陷入贫困和犯罪》,9 年 2017 月 8 日,《经济学人》)。 [XNUMX]
奥莱因卡·阿贾拉 (Olayinka Ajala) 将新游牧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牲畜所有权形式,其特征是非游牧民族拥有大群牲畜。 因此,这些羊群由雇佣的牧羊人服务。 在这些畜群周围开展工作通常需要使用先进的武器和弹药,因为需要隐藏被盗的财富、贩运所得或通过恐怖活动获得的收入,其明确目的是为投资者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阿贾拉·奥莱因卡 (Ajala Olayinka) 对非畜牧业的定义不包括通过合法手段融资的牛投资。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数量较少,不属于作者的研究兴趣范围。 [5]
放牧游牧畜牧业传统上规模较小,畜群为家庭所有,通常与特定种族群体相关。 这种农业活动伴随着各种风险,并且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将牲畜迁移数百公里寻找牧场。 所有这些使得这个职业不那么受欢迎,并且有几个民族从事这个职业,其中富拉尼人脱颖而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他们的主要职业。 除了是萨赫勒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族群之一之外,一些消息来源称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约有 17 万人。 此外,牛通常被视为安全的来源和财富的指标,因此传统牧民从事牛的销售规模非常有限。
传统田园主义
新游牧主义在牲畜所有制形式、畜群平均规模、武器使用等方面与传统游牧主义有所不同。 传统的平均牛群规模在 16 到 69 头牛之间,而非游牧牛群的规模通常在 50 到 1,000 头牛之间,而他们周围的交战往往涉及雇佣牧民使用枪支。 [8], [5]
尽管以前在萨赫勒地区,如此大规模的牛群由武装士兵陪同的情况很常见,但如今,牲畜所有权越来越被视为向腐败政客隐瞒不义之财的一种手段。 此外,虽然传统的牧民努力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以维持与农民的共生互动,但雇佣牧民却没有动力投资于与农民的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拥有可以用来恐吓农民的武器。 [5], [8]
特别是在尼日利亚,新田园主义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由于价格不断上涨,牲畜所有权似乎是一项诱人的投资。 在尼日利亚,一头性成熟的奶牛售价为 1,000 美元,这使得奶牛养殖成为对潜在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领域。 [5]
其次,新田园主义与尼日利亚的腐败行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腐败是该国大多数叛乱和武装叛乱的根源。 2014年,政府出台了一项遏制腐败,特别是洗钱的措施。 这是银行验证号 (BVN) 条目。 BVN 的目的是监控银行交易并减少或消除洗钱活动。 [5]
银行验证码 (BVN) 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在所有尼日利亚银行注册每位客户。 然后,每个客户都会获得一个唯一的识别码,该识别码链接到他们的所有帐户,以便他们可以轻松监控多家银行之间的交易。 其目的是确保通过系统捕获所有银行客户的图像和指纹,轻松识别可疑交易,从而使非法资金难以被同一人存入不同账户。 深入采访的数据显示,BVN 使政治官员更难隐藏非法财富,许多与政客及其亲信有关的账户在其推出后被冻结,这些账户涉嫌被盗资金。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报告称,“数十亿奈拉(尼日利亚货币)和数百万其他外币被困在多家银行的账户中,这些账户的所有者突然停止与他们开展业务。 自 30 年尼日利亚引入 BVN 以来,最终已识别出超过 2020 万个“被动”和未使用帐户。 [5]
笔者的深度采访发现,在银行验证码(BVN)推出之前,许多在尼日利亚银行存入大笔资金的人都急于提取。 在任何使用银行服务获得 BVN 的截止日期前几周,尼日利亚的银行官员目睹了名副其实的现金从该国各个分行大量兑现。 当然,不能说所有这些钱都是被盗或滥用权力的结果,但尼日利亚许多政客因为不想受到银行监控而转向支付现金,这是既定的事实。 [5]
此时此刻,非法资金流向农业部门,大量牲畜被购买。 金融安全专家一致认为,自引入 BVN 以来,使用不义之财购买牲畜的人数急剧增加。 考虑到2019年一头成年牛的价格为200,000万至400,000万奈拉(600至110美元),而且没有建立牛所有权的机制,腐败分子很容易用数百万奈拉购买数百头牛。 这导致牲畜价格上涨,许多大型牛群现在由那些与养牛作为工作和日常生活无关的人拥有,其中一些所有者甚至来自距离放牧太远的地区地区。 [5]
如上所述,这给牧场地区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安全风险,因为雇佣牧民往往装备精良。
第三,新牧民解释了业主和牧民之间的新世袭关系的新模式,以及从事该行业的贫困程度的增加。 尽管过去几十年牲畜价格不断上涨,出口市场畜牧业不断扩大,但流动畜牧农民的贫困并未减少。 相反,根据尼日利亚研究人员的数据,在过去的30-40年里,贫困牧民的数量急剧增加。 (Catley、Andy 和 Alula Iyasu,搬迁还是迁出?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地区 Shinile 区 Mieso-Mulu Woreda 的快速生计和冲突分析,2010 年 XNUMX 月,范斯坦国际中心)。
对于牧区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为大畜群的主人工作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 在新牧区环境中,牧民社区日益贫困,导致传统的流动牧民破产,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缺席业主”的廉价劳动力的猎物。 在一些政治内阁成员拥有牛群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参与这一活动的牧区成员或特定民族的牧民,往往以“支持当地”的资金形式获得报酬。社区”。 这样,非法所得的财富就合法化了。 这种庇护关系在尼日利亚北部(这里是包括富拉尼人在内的传统移徙牧民数量最多的地方)尤为普遍,他们被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当局的帮助。 [5]
在本案例中,阿贾拉·奥莱因卡 (Ajala Olayinka) 以尼日利亚为例,深入探讨这些新的冲突模式,因为尼日利亚是西非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牲畜最集中的国家,约有 20 万头牲畜。牛。 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牧民数量也非常多,该国的冲突规模也非常严重。 [5]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也是关于农业重心和游牧移民农业的地理转移以及与之相关的冲突,从过去最提倡的非洲之角国家到西非和尤其是尼日利亚。 无论是牲畜饲养量还是冲突规模都在逐渐从非洲之角国家向西方转移,目前问题的焦点在尼日利亚、加纳、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科特迪瓦等国家。 '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 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得到了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的数据的充分证实。 同样,根据同一消息来源,尼日利亚的冲突和随后的死亡人数领先于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国家。
Olayinka 的研究结果基于实地研究和定性方法的使用,例如 2013 年至 2019 年在尼日利亚进行的深度访谈。 [5]
从广义上讲,该研究解释说,传统畜牧业和迁徙畜牧业正在逐渐让位于新畜牧业,新畜牧业是一种畜牧业形式,其特点是畜群规模大得多,并更多地使用武器和弹药来保护它们。 [5]
尼日利亚非畜牧业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事件数量严重增加,从而导致农村地区牲畜盗窃和绑架的动态增加。 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并且已经被观察到很长时间了。 阿齐兹·奥兰尼安 (Aziz Olanian) 和亚哈亚·阿利尤 (Yahaya Aliyu) 等研究人员表示,几十年来,偷牛行为“是局部性的、季节性的,并且使用更传统的武器,暴力程度较低”。 (Olaniyan、Azeez 和 Yahaya Aliyu,《奶牛、强盗和暴力冲突:了解尼日利亚北部的偷牛行为》,载于:《非洲光谱》,第 51 卷,第 3 期,2016 年,第 93 – 105 页)。
他们认为,在这段漫长(但看似早已过去)的时期,偷牛行为与游牧民的福祉息息相关,偷牛行为甚至被视为“牧民重新分配资源和扩张领土的工具”。 ”。 。
为了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牧区领导人制定了禁止偷牛行为的规则(!),不允许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 偷牛期间的杀戮也被禁止。
正如 Olanian 和 Aliyu 报道的那样,这些规则不仅在西非实行,而且在东非、非洲之角以南也实行,例如在肯尼亚,瑞安·特里谢 (Ryan Trichet) 报告说肯尼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Triche,Ryan,《肯尼亚的田园冲突:将图尔卡纳和波科特社区之间的模仿暴力转变为模仿祝福》,《非洲冲突解决杂志》,第 14 卷,第 2 期,第 81-101 页)。
当时,特定民族(其中以富拉尼族为代表)从事迁徙畜牧业和畜牧业,他们生活在高度联系和交织的社区中,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这有助于解决由此产生的争端和冲突。 。 解决问题而不升级为极端形式的暴力。 [5]
几十年前和今天的偷牛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偷牛行为背后的逻辑。 过去,偷牛的动机要么是为了挽回一些家畜损失,要么是为了支付婚礼彩礼,要么是为了平均一些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形象地说“不是市场导向的”。盗窃的主要动机不是追求任何经济目标”。 这种情况在西非和东非都存在。 (Fleisher, Michael L.,“战争有利于偷窃!”:坦桑尼亚库里亚地区犯罪与战争的共生,非洲:国际非洲研究所杂志,第 72 卷,第 1 期,2002 年,第 131 页-149)。
过去十年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目睹的牲畜盗窃事件主要是出于经济繁荣的考虑,形象地说是“市场导向”。 它大多是为了利润而被盗,而不是出于嫉妒或极端需要。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方法和做法的传播也可以归因于诸如牲畜成本上涨、人口增长导致的肉类需求增加以及武器容易获得等情况。 [5]
阿齐兹·奥兰尼安 (Aziz Olanian) 和叶哈亚·阿利尤 (Yahaya Aliyu) 的研究毫无争议地确立并证明了新游牧主义与尼日利亚牲畜盗窃数量增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几个非洲国家发生的事件加剧了该地区的武器扩散(扩散),雇佣兵新牧民获得了“畜群保护”武器,这些武器也被用于盗窃牛群。
武器扩散
2011年之后,这一现象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当时数以万计的小武器从利比亚蔓延到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这些观察结果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专家小组”的充分证实,该小组还对利比亚冲突进行了审查。 专家指出,利比亚的起义和随后的战斗导致武器空前扩散,不仅在利比亚邻国,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
联合国安理会专家收集了14个非洲国家的详细数据,他们表示,尼日利亚是受利比亚武器猖獗扩散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武器通过中非共和国(CAR)走私到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这些货物加剧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冲突、不安全和恐怖主义。 (斯特拉扎里、弗朗西斯科,《利比亚武器与地区不稳定》,《国际观察家》。意大利国际事务杂志,第 49 卷,第 3 期,2014 年,第 54-68 页)。
尽管利比亚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洲武器扩散的主要根源,但其他活跃的冲突也助长了武器流向不同群体,包括尼日利亚和萨赫勒地区的新牧民。 这些冲突包括南苏丹、索马里、马里、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据估计,截至 2017 年 100 月,全球危机地区有超过 XNUMX 亿件小武器和轻武器 (SALW),其中很大一部分在非洲使用。
非法军火贸易行业在非洲蓬勃发展,大多数国家的边界都存在“漏洞百出”的情况,武器可以在边界上自由流动。 虽然大多数走私武器最终落入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手中,但流动牧民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 例如,苏丹和南苏丹的牧民十多年来一直公开展示他们的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 尽管在尼日利亚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传统牧民手持棍棒放牧,但一些移民牧民被发现携带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有些人被指控参与偷牛活动。 过去十年来,偷牛事件大幅增加,不仅导致传统牧民死亡,还造成农民、安全人员和其他公民死亡。 (Adeniyi、Adesoji,非洲不受控制的武器造成的人员伤亡,对七个非洲国家的跨国研究,10 年 2017 月,乐施会研究报告)。
除了雇用的牧民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从事盗牛活动外,尼日利亚部分地区还有主要从事武装盗牛活动的职业土匪。 新牧民在解释牧民武装时,常常声称自己需要保护,免受这些土匪的侵害。 一些接受采访的牲畜饲养者表示,他们携带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强盗袭击,这些强盗意图偷走他们的牛。 (Kuna、Mohammad J. 和 Jibrin Ibrahim(编辑),尼日利亚北部的农村土匪和冲突,民主与发展中心,阿布贾,2015 年,ISBN:9789789521685、9789521685)。
尼日利亚 Miyetti Allah 牲畜饲养者协会(该国最大的牲畜饲养者协会之一)的国家秘书表示:“如果你看到一名富拉尼人携带 AK-47,那是因为偷牛行为变得如此猖獗,以至于他想知道这个国家是否有任何安全”。 (富拉尼民族领袖:为什么我们的牧民携带AK47,2年2016月1日下午58点XNUMX分,新闻)。
问题在于,为防止偷牛而获得的武器在牧民与农民之间发生冲突时也被随意使用。 这种围绕迁徙牲畜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军备竞赛,并造成了战场般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传统牧民也开始携带武器与牲畜一起自卫。 不断变化的动态正在导致新一波的暴力,通常统称为“牧区冲突”。 [5]
农牧民之间严重冲突和暴力的数量和强度的增加也被认为是新牧民主义发展的结果。 排除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农牧民之间的冲突占2017年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最多。(Kazeem,Yomi,尼日利亚现在的内部安全威胁比博科圣地更大,19年2017月XNUMX日,Quarz)。
尽管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冲突和不和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之前,但这些冲突的动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Ajala,Olayinka,为什么萨赫勒地区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2 年 2018 月 2.56 日,欧洲中部夏令时间下午 XNUMX 点 XNUMX 分,《对话》)。
在前殖民时期,由于农业的形式和畜群的规模,牧民和农民常常共生共生。 牲畜在农民收割后留下的残茬上吃草,最常见的是在旱季,迁徙的牧民将牲畜迁往更南的地方去那里吃草。 为了换取农民给予的有保证的放牧和使用权,牛粪被农民用作农田的天然肥料。 这是小农农场和家庭拥有牛群的时代,农民和牧场主都从他们的理解中受益。 有时,当放牧牲畜毁坏农产品并引发冲突时,当地会实施冲突解决机制,消除农牧民之间的分歧,通常不会诉诸暴力。 [5] 此外,农民和流动牧民经常制定粮换奶计划来加强他们的关系。
然而,这种农业模式经历了多次变化。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人口爆炸、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气候变化、乍得湖面积缩小、土地和水的竞争、迁徙牧区使用权、干旱等问题沙漠的扩大(荒漠化)、种族分化的加剧和政治操纵被认为是农民与流动牲畜饲养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原因。 大卫海塞尔和卢纳认为,非洲殖民化和市场资本主义关系的引入是非洲大陆牧民和农民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Davidheiser、Mark 和 Aniuska Luna,从互补到冲突:西非 Farmet-Fulbe 关系的历史分析,《非洲冲突解决杂志》,第 8 卷,第 1 期,2008 年,第 77 – 104 页)。
他们认为,殖民时代发生的土地所有权法的变化,加上采用现代农业方法(如灌溉农业)和引入“使流动牧民适应定居生活的计划”后农业技术的变化,违反了《土地法》的规定。农民和牧民之间以前的共生关系,增加了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大卫海塞尔和卢纳的分析认为,市场关系与现代生产方式的融合导致了农牧民之间从“交换关系”向“市场化和商品化”(即生产商品化)的转变,两国之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压力,破坏了先前的共生关系。
气候变化也被认为是西非农牧民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0年在尼日利亚卡诺州进行的一项定量研究中,哈利鲁指出,沙漠对农田的侵占是导致尼日利亚北部牧民和农民之间冲突的资源争夺的主要根源。 (Halliru,Salisu Lawal,尼日利亚北部农民和养牛者之间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卡诺州库拉地方政府三个社区的案例研究。见:Leal Filho,W.(编辑)气候变化适应手册,施普林格,柏林,海德堡,2015)。
降雨量的变化改变了牧民的迁徙模式,牧民进一步向南迁徙,进入了过去几十年牧群通常不会放牧的地区。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苏丹-萨赫勒沙漠地区长期干旱的影响,该地区自 1970 年以来变得更加严重。(Fasona、Mayowa J. 和 AS Omojola,尼日利亚的气候变化、人类安全和社区冲突,22 月 23 日至 2005 日XNUMX 年,人类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霍尔门峡湾酒店,奥斯陆附近的阿斯克,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 (GECHS),奥斯陆)。
这种新的迁移模式增加了对土地和土壤资源的压力,导致农牧民之间的矛盾。 在其他情况下,农牧区人口的增加也加剧了对环境的压力。
尽管这里列出的问题导致了冲突的加深,但过去几年在冲突的强度、使用的武器类型、攻击方式和死亡人数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过去十年中,袭击次数也显着增加,尤其是在尼日利亚。
ACLED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自 2011 年以来,冲突变得更加严重,突显出冲突可能与利比亚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武器扩散有关。 尽管大多数受利比亚冲突影响的国家的袭击次数和伤亡人数有所增加,但尼日利亚的数字证实了袭击增加的规模和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利比亚冲突的情况。冲突的关键要素。
奥拉因卡·阿贾拉 (Olayinka Ajala) 认为,袭击的方式和强度与非畜牧业之间有两个主要关系。 首先是牧民使用的武器弹药类型,其次是参与袭击的人员。 [5] 他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当牧民在放牧路线上存在分歧或流动牧民破坏农田时,牧民购买的用于保护牲畜的武器也会被用来攻击农民。 [5]
奥莱因卡·阿贾拉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袭击者使用的武器类型给人的印象是移民牧民得到了外部支持。 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塔拉巴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该州牧民长期发动袭击后,联邦政府已在受影响社区附近部署士兵,以防止进一步袭击。 尽管在受影响社区部署了部队,但仍有几起袭击事件使用了包括机枪在内的致命武器。
塔拉巴州塔库姆地区地方政府主席希班·蒂卡里先生在接受《尼日利亚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拿着机枪来到我们社区的牧民并不是我们所认识和接触的传统牧民。”连续多年; 我怀疑他们可能是被释放的博科圣地成员。 [5]
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部分牧民社区已全副武装,现在正在充当民兵。 例如,牧民社区的一位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吹嘘说,他的组织已成功对尼日利亚北部的几个农业社区发动了袭击。 他声称他的组织不再害怕军队,并表示:“我们有 800 多支(半自动)步枪、机枪; 富拉尼人现在拥有炸弹和军服。” (萨尔基达,艾哈迈德,富拉尼牧民独家报道:“我们有机枪、炸弹和军装”,Jauro Buba;07 年 09 月 2018 日)。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Olayinka Ajala 采访的许多其他人的证实。
牧民袭击农民所使用的武器弹药是传统牧民所没有的,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对新牧民的怀疑。 在接受一名军官采访时,他声称拥有小牧群的贫困牧民买不起自动步枪和袭击者使用的武器类型。 他说:“我想,一个贫穷的牧民怎么买得起这些袭击者使用的机枪或手榴弹?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成本效益分析,当地牧羊人无法投资此类武器来保护他们的小羊群。 对于花巨资购买这些武器的人来说,他们要么在这些牛群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要么打算偷走尽可能多的牛来收回投资。 这进一步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卡特尔现在参与了迁徙牲畜”。 [5]
另一位受访者表示,传统牧民买不起AK47的价格,AK1,200在尼日利亚黑市上的售价为1,500美元至2017美元。 此外,5,000 年,众议院代表三角洲州(南南地区)的议员埃文斯·伊武里 (Evans Ivuri) 表示,一架身份不明的直升机定期向该州奥雷-阿布拉卡荒野的一些牧民运送货物,他们在那里与他们的牲畜住在一起。 据立法者称,森林里居住着2,000多头牛和约XNUMX名牧羊人。 这些说法进一步表明这些牛的所有权非常值得怀疑。
奥莱因卡·阿贾拉 (Olayinka Ajala) 表示,袭击的模式和强度与非畜牧业之间的第二个联系是参与袭击的人的身份。 关于参与袭击农民的牧民身份存在多种说法,其中许多袭击者就是牧民。
在许多农民和牧场主共存了几十年的地区,农民知道哪些牧场主的牛群在他们的农场周围放牧,他们携带牲畜的时间以及牛群的平均规模。 如今,有人抱怨牧群规模更大,牧民对农民来说很陌生,并且配备了危险武器。 这些变化使得农牧民冲突的传统管理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5]
塔拉巴州乌萨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Rimamsikwe Karma先生表示,对农民进行一系列袭击的牧民并不是当地人所认识的普通牧民,称他们是“陌生人”。 委员会主席表示,“跟随军队来到我们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牧羊人对我们的人民并不友好,对我们来说,他们是陌生人,他们杀人”。 [5]
这一说法得到了尼日利亚军方的证实,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参与暴力和袭击农民的移民牧民是受到“赞助”的,而不是传统牧民。 (Fabiyi、Olusola、Olaleye Aluko 和 John Charles,《贝努埃:杀手牧民受到赞助》,军方称,27 年 2018 月 XNUMX 日,Punch)。
卡诺州警察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许多被捕的武装牧民来自塞内加尔、马里和乍得等国家。 [5] 这进一步证明越来越多的雇佣牧民正在取代传统牧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并非全部都是新牧民主义造成的。 最近的事件表明,许多传统的流动牧民已经携带武器。 此外,针对农民的一些袭击是对农民杀害牲畜的报复和报复。 尽管尼日利亚不少主流媒体声称牧民是大部分冲突的侵略者,但深入采访发现,部分针对定居农民的袭击是为了报复农民杀害牧民的牲畜。
例如,高原州的贝罗姆族(该地区最大的族群之一)从不掩饰对牧民的蔑视,有时甚至会通过宰杀牲畜来阻止他们的土地上放牧。 这导致牧民的报复和暴力,导致贝罗姆族社区数百人被屠杀。 (Idowu,Aluko Opeyemi,尼日利亚城市暴力维度:农民和牧民的攻击,AGATHOS,第 8 卷,第 1 期(14),2017 年,第 187-206 页); (Akov,Emmanuel Terkimbi,重新审视资源冲突辩论:解开尼日利亚中北部地区农牧民冲突案件,第 26 卷,2017 年,第 3 期,《非洲安全评论》,第 288 – 307 页)。
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针对农民的袭击,一些农业社区组建了巡逻队以防止对其社区的袭击,或对牧群社区发起反击,进一步加剧了各群体之间的敌意。
最终,尽管统治精英普遍了解这场冲突的动态,但政治家往往在反映或掩盖这场冲突、潜在解决方案以及尼日利亚政府的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已经详细讨论了牧场扩张等潜在解决方案; 解除武装牧民的武装; 为农民带来好处; 农业社区的安全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和斗牛贼,这场冲突充满了政治算计,自然使其解决起来十分困难。
关于政治账目,有几个问题。 首先,将这种冲突与种族和宗教联系起来往往会转移人们对根本问题的注意力,并在先前融合的社区之间造成分裂。 虽然几乎所有牧民都是富拉尼人,但大多数袭击都是针对其他族裔群体。 政客们经常强调冲突的种族动机,而不是解决冲突背后的问题,以提高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并像尼日利亚其他冲突那样创造“庇护”。 (Berman,Bruce J.,种族、庇护和非洲国家:不文明民族主义的政治,第 97 卷,第 388 期,非洲事务,1998 年 305 月,第 341 – 42 页); (Arriola, Leonardo R.,《非洲的赞助与政治稳定》,第 10 卷,第 2009 期,比较政治研究,XNUMX 年 XNUMX 月)。
此外,强大的宗教、种族和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大力解决问题的同时进行政治和种族操纵,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紧张局势。 (普林斯威尔,塔比亚,《穷人痛苦的政治:牧民、农民和精英操纵》,17 年 2018 月 XNUMX 日,先锋集团)。
其次,关于放牧和牧场的争论常常被政治化,并以一种倾向于富拉尼人被边缘化或富拉尼人受到优惠待遇的方式描绘,这取决于谁参与了争论。 2018年179月,在几个受冲突影响的州决定分别在其领土上引入反放牧法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试图结束冲突并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宣布计划花费600亿奈拉(约10亿美元)用于在该国十个州建设“牧场”型畜牧场。 (奥博戈、奇内洛、21 个州拟议的养牛场引起轩然大波。伊博人、中带、约鲁巴团体拒绝 FG 的计划,2018 年 XNUMX 月 XNUMX 日,《太阳报》)。
尽管牧民社区以外的一些团体认为牧业是私营企业,不应承担公共支出,但流动牧民社区也拒绝了这一想法,理由是它旨在压迫富拉尼社区,影响富拉尼人的迁徙自由。 几位畜牧界成员声称,拟议的畜牧法“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在 2019 年选举中赢得选票的竞选活动”。 [5]
该问题的政治化,加上政府的随意态度,使得任何解决冲突的步骤对有关各方都没有吸引力。
第三,尼日利亚政府不愿取缔那些声称对袭击农业社区负责以报复杀害牲畜的组织,这与担心庇护关系破裂有关。 尽管尼日利亚 Miyetti Allah 养牛者协会 (MACBAN) 辩称 2018 年在高原州杀害数十人是对农业社区杀害 300 头牛的报复,但政府拒绝对该组织采取任何行动,声称该组织代表富拉尼人利益的社会文化团体。 (Umoru、Henry、Marie-Therese Nanlong、Johnbosco Agbakwuru、Joseph Erunke 和 Dirisu Yakubu,高原大屠杀,对失去 300 头牛的报复 – Miyetti Allah,26 年 2018 月 XNUMX 日,Vanguard)。这导致许多尼日利亚人认为该组织是由于当时的现任总统(布哈里总统)来自富拉尼族,因此有意受到政府的保护。
此外,尼日利亚统治精英无力应对冲突的新牧区影响,也带来了严重问题。 政府没有解决畜牧业日益军事化的原因,而是关注冲突的种族和宗教层面。 此外,许多大群牛的主人属于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权贵阶层,导致犯罪活动难以起诉。 如果没有正确评估冲突的新牧区层面,没有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该国的局势可能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们甚至会看到局势的恶化。
使用的来源:
分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使用的文献的完整列表在分析第一部分的末尾给出,以“萨赫勒——冲突、政变和移民炸弹”为标题发表。 下面仅给出分析的第三部分中引用的来源——“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新牧区主义和圣战主义”。
文中给出了其他来源。
[5] Ajala,Olayinka,尼日利亚冲突的新驱动因素:对农民和牧民之间冲突的分析,《第三世界季刊》,第 41 卷,2020 年,第 12 期,(09 年 2020 月 2048 日在线发布),第 2066-XNUMX 页,
[8] Brottem、Leif 和 Andrew McDonnell,《苏丹-萨赫勒地区的畜牧业与冲突:文献综述》,2020 年,寻找共同点,
[38]桑加雷、布卡里、萨赫勒和西非国家的富拉尼人和圣战主义,8年2019月XNUMX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和萨赫勒观察站,战略研究基金会(FRS)。
摄影:Tope A. Asokere: https://www.pexels.com/photo/low-angle-view-of-protesters-with-a-banner-5632785/
关于作者的说明:
Teodor Dechev 自 2016 年起担任普罗夫迪夫(保加利亚)安全与经济高等学院 (VUSI) 的全职副教授。
他曾在新保加利亚大学索非亚分校和VTU“圣彼得堡”大学任教。 圣西里尔和迪乌斯”。 他目前在 VUSI 和 UNSS 任教。 他的主要教学课程有:劳资关系与安全、欧洲劳资关系、经济社会学(英语和保加利亚语)、民族社会学、民族政治和民族冲突、恐怖主义和政治暗杀——政治和社会学问题、组织的有效发展。
他是超过 35 部有关建筑结构耐火性和圆柱形钢壳耐火性的科学著作的作者。 他是 40 多本社会学、政治学和劳资关系著作的作者,包括专着:劳资关系和安全 – 第 1 部分。集体谈判中的社会让步(2015 年); 制度互动和劳资关系(2012); 私营保安部门的社会对话(2006 年); “灵活的工作形式”和中欧和东欧的(后)劳资关系(2006 年)。
他与人合着了《集体谈判的创新》一书。 欧洲和保加利亚方面; 保加利亚雇主和工作中的妇女; 保加利亚生物质利用领域的社会对话和妇女就业。 最近,他一直在研究劳资关系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球恐怖主义瓦解的发展; 民族社会学问题、民族和民族宗教冲突。
国际劳工和就业关系协会(ILERA)、美国社会学协会(ASA)和保加利亚政治学协会(BAPN)会员。
具有政治信念的社会民主党人。 1998年至2001年,担任劳工和社会政策部副部长。 1993 年至 1997 年担任《人民自由报》主编。2012 年至 2013 年担任《人民自由报》社长。2003 年至 2011 年担任 SSI 副主席和主席。 AIKB 自 2014 年至今。 2003年至2012年担任NSTS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