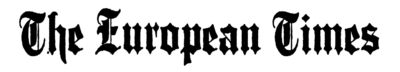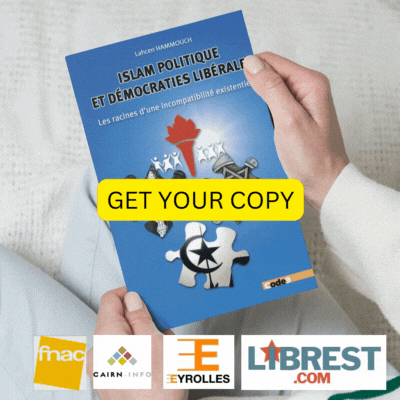列昂尼德·邬斯宾斯基
13世纪和14世纪,借用古代的数量大大增加,借用的古代图案进入教堂艺术不再只是作为补充; 它们渗透到情节本身及其性格中。 人们倾向于通过深度来赋予体积。 出现了某种风格主义,描绘背面、侧面、透视、透视。 旧约中的故事变得特别受欢迎。 其中有圣母像(例如未燃的黑莓、基甸的羊毛)、基督的像(例如亚伯拉罕、麦基洗德),以及一些象征性的基督像(以天使的形式)。 教堂的装饰失去了前一时期所特有的严格统一和巨大简洁性。 这不是一个放弃教条原则的问题,而是它与建筑的有机联系开始受到干扰。 “肖像画家和马赛克艺术家不再服从寺庙的内部空间……来揭示其意义。 他们将无数的图像并置在一起”。 一种本质上是空间的艺术,迄今为止更多地传达了关系而不是手势,更多的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连串的情感,现在涉及到时间流动的内容的传达:叙述,叙述,心理反应等。 。 所描绘的人物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描绘的是单个人物还是复杂的构图,它不再总是向外,面向在其面前祈祷的信徒。 通常,图像的展开就像一幅拥有自己生命的图画,仿佛自我封闭,与观看者无关。
当时,祭坛隔板上的图像也增多,其主题必定与教会主要圣事——圣体圣事的意义直接相关。 在其比喻性的解释中,出现了两种潮流:一方面,寻找一个连贯的神学体系,通过图像的方式揭示了我们救赎的整个内务。 这种趋势导致了圣像屏风主题的形成,其古典形式形成于15世纪的俄罗斯。 另一方面,有一种趋势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即以图像来阐明圣礼的含义,说明礼仪中的各个时刻,例如大入口。 正是在这个图像主题中,可成像与不可成像之间的界限经常被侵犯。 例如,有一个场景是牧师将躺在铁饼上的圣婴供奉——这个场景达到了极端自然主义,让人想起一场谋杀仪式(塞尔维亚马泰伊的 14 世纪教堂)。 不可否认的是,铁饼上的圣婴主题是对十二世纪礼仪争议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西方神学家阵营的回响。 到了古学家时代,此类争论显然已经在人文主义者关于理性主义的智慧被劫持的沃土上滋长起来。
除了礼拜仪式各个时刻的插图外,还出现了许多图像主题,显然是为了通过偷来的象征图像来揭示圣礼的含义:索菲亚的桌子(智慧的宴会),或索菲亚智慧使徒的圣餐,这些主题形象地再现了《所罗门箴言》9:1-6 中的文本——“智慧建造了她的房屋”。 文本以两幅图呈现。 一方面,索菲亚智慧 – 天使 – 根据古代拟人化类型的神圣智慧的化身:另一方面 – 基督 – 大议会天使形式的智慧。 必须记住,在静修派和他们的对手之间的争论中,智慧这个话题相当普遍。 毫无疑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索菲亚·智慧的象征形象在古学家时代传播开来。 在这一象征主义中,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人文复兴的影响。 虽然它与静修派的思想并不相符,但这种象征意义以及对古代的借鉴并不总是对静修派来说是陌生的。 对智慧的象征性描述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可以被理解为静修派试图将上帝的智慧与哲学家的智慧对立起来。 这种类型的象征主义,无论艺术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都会破坏真正的东正教关于圣像的教义,并导致违反教会规则,特别是第五至第六届理事会的第 82 条规则。
我们记得,这条规则删除了那些取代道成肉身的直接形象的符号:“尊重古代的形象和影子作为真理的标志和类型……,我们现在更喜欢恩典和真理,它们是律法的实现”。 现在,在古时代,这种“道成肉身”违反了福音派现实主义的原则,在圣体主题的情况下尤其矛盾。 作为被绑架思想的成果,这种象征主义并不符合传统的正统思想,就像它不符合可想象与不可想象的混合一样。
象征性图像取代了直接的人类形象,对情感生活的表现性艺术反映,对希腊化自然主义的渴望,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图像主题,以及旧约类型的繁衍——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成果。新思想汹涌的时代,人文主义与静谧主义复兴的时代。 如果说传统艺术家并不总是免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那么人文主义的同情者反过来也没有离开以静修主义为代表的东正教艺术的传统形式。 古文艺复兴并没有放弃这些传统形式。 但在时代观念的影响下,一些元素渗透到其中,降低了图像的灵性,有时甚至破坏了图像的概念本身、它的意义,以及它在教会中的功能。 这些思想是基于世界物质知识的上帝抽象思想的成果,与东正教传统相关,就像人文世界观与传统静修方法相关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对哲学和精神生活世俗知识的重视和重视,另一方面对它们采取静观的态度,可以给我们间接的信号来理解双方对教会的看法。艺术。
圣格雷戈里·帕拉马斯在与人文主义者的争论中写道:“如果任何人愿意,我们不会阻止他熟悉世俗的科学,除非他过上了修道院的生活。 但我们建议不要对它们研究得太深,并严格禁止期望获得关于神圣事物的准确知识,因为没有人能从它们中得出关于上帝的真正教导。”
我们进一步读到:“确实,世俗哲学家中有些东西是有用的,就像蜂蜜中有毒草的花粉一样。 但存在很大的危险,那些想要将蜂蜜与苦草分开的人会意外地吞下有毒的残留物。” 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详细论述了世俗科学与一般哲学以及上帝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尽管有上述敏锐的判断,他并不否认世俗知识的重要性,甚至承认它是比较有用的。 和巴拉姆一样,他认为这是间接地、相对地认识上帝的方法之一。 但他顽固地拒绝宗教哲学和世俗知识作为与上帝交流和认识上帝的手段。 科学不仅无法给出“关于上帝的任何真实教导”,而且当应用于不适合它的领域时,它会导致歪曲,而且,它会阻碍与上帝真正的交流; 可能是“致命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圣格雷戈里·帕拉马斯只保护与上帝交流的领域不与宗教哲学和自然即上帝的自然知识相混合。 从这种静谧的态度出发,将世俗科学和宗教哲学与神学领域相结合,可以得出结论,教会艺术的任务和功能就是这样设定的。
必须说的是,如果在静修者的心身技术中可以注意到对图像的某种公正性,那么他们对圣像崇拜的态度以及圣像在崇拜和祈祷中的重要性仍然完全符合东正教教义。 圣格列高利在谈到圣像时,不仅表达了古典东正教的观点,而且还添加了一些静修教义特征和东正教艺术大方向的澄清。 他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的那位,出于对他的爱,创造了一个圣像,通过它敬拜他,通过它让你的思绪转向救主,他在荣耀中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崇拜谁。 以同样的方式,为圣人创造圣像……并且不要将他们当作神来崇拜——这是被禁止的,而是作为你与他们交流的见证,对他们的爱,为了他们的荣誉,通过他们的圣像提升你对他们的思想”。
可以看出,圣格列高利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对其基础和内容的理解上都表达了传统的东正教教义。 但在他的神学背景下,这个内容听起来带有典型的灵气学时期的特征。 对于圣格列高利来说,道成肉身是期望结出果实的起点:神圣的荣耀以神的道的人形显现出来。 基督神化的身体已经接受并赐给我们神性永恒的荣耀。 正是这个形象被描绘在圣像上并被崇拜到揭示基督神性的程度。 由于神和圣徒有同样的恩典,他们的形象也是“按样式”造的。
鉴于对图像的这种态度及其对其内容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静修者来说,唯一可以作为与上帝交流的手段的图像是反映与上帝和谐共融的体验的图像。静谧的教导。 基于抽象思维和对世界的经验感知的艺术元素,就像哲学和世俗科学一样,无法给出“任何关于上帝的真实教导”。 对耶稣基督的象征性描绘取代了神圣荣耀持有者的个人形象,破坏了圣像作为上帝道成肉身见证的教学基础。 因此,这样的圣像不能“让人想到站在父神的右边的救世主”。 很自然,随着静修主义的胜利,教会结束了邪教艺术中的那些元素,这些元素以某种方式破坏了其教义。 正是由于休憩,“最后的拜占庭人与意大利人不同,他们让位于自然性,但没有将其转变为自然主义; 他们使用深度,但不将其锁定在透视法则中; 探索人类,但不要将其与神圣隔离”。 艺术保留了与启示的联系,并保留了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协同本质。
圣格雷戈里·帕拉马斯关于与神圣能量共融本质的教导“摧毁了理性主义和反传统实证主义的所有残余”,也揭示了在圣像崇拜教导中值得注意的更遥远的问题。 进一步的教义工作只能通过表达精神体验的内容以及教会艺术的内容来进行。 在圣像崇拜的教条中,人们认识到艺术家可以通过形式、颜色、线条将神圣行动的结果转化为人类; 并且这个结果可以被显示出来,变得明显。 在塔博尔之光的教导中,人们认识到这种改变人类的神圣行动是非受造且不朽的光,是通过感官感受和沉思的神圣能量。 因此,神圣能量的教义与圣像的教义融为一体。 正如在关于塔博尔之光的争论中,给出了对人的神化的教条主义表述一样,对圣像的内容也给出了教条主义的辩护。 这是定义这些框架的时候,教会艺术在不停止其教会性的情况下就不能落后。
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教义的胜利对于东正教的进一步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果教会在人文主义的猛攻面前保持被动,那么这个时代新思想的飓风无疑会导致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危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新异教。
与新的哲学——因此也证实了完全不同的教堂艺术方式。
如果说,由于静修主义,教堂艺术没有跨越界限,超出了界限,它就不再表达东正教教义,然而,在 14 世纪下半叶,定义古生物学复兴的活生生的创造性传统开始让位于一种保守主义。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地区后,教堂艺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转移到了俄罗斯。 静修主义的生机勃勃的冲动和塑造东正教人类学的教条,帕拉姆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教义,将在俄罗斯艺术和精神生活中结出无价的果实。 在那里,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繁荣有着与拜占庭古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基础。 保守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将无力抵抗来自西方的推动。 S.拉多伊契奇有权利说:“西方影响对拜占庭艺术的损害比土耳其人更大”。
1351 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是教会确认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教义的最庄严的行动。 十四世纪见证了整个东正教教会如何接受该委员会的决定。 会议一年后,其决定被提升为正教庄严的规范继承。 1368 年,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去世后不久,他被封为圣人。 14 月 843 日是纪念他的日子。大斋节的第二个星期日也是为了纪念他作为“神圣之光的传道者”(晚祷,第三节)。 在这里,他被歌颂为“东正教的杰出人物、教会的导师和支柱”(tropar)。 因此,周日之后,东正教庆祝宣布人神化的教义。 XNUMX年的大公会议结束了教会历史上的基督论时期,在礼仪上与圣灵论时期的顶峰联系在一起。
资料来源:列昂尼德·邬斯宾斯基。 圣像神学,卷。 I 和 II,纽约: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出版社,199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