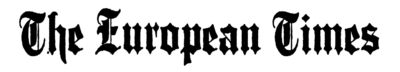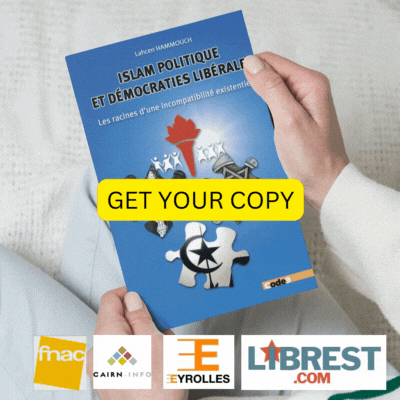戰後,美國出版業中有如此多的猶太人,以至於一些作家開始創造一個詞來形容他們:“文學黑手黨”。
他們認為,這個黑手黨秘密確保猶太書籍和作者將由主要出版社出版,由文學出版社報導並得到主要學術機構的支持——以犧牲其他非猶太作家,甚至“錯誤”的猶太作家。
這種信念,有時是由反猶太主義驅動,有時是由文學流離失所和職業挫折感所驅動,被包括在內的人物所認同 杜魯門·卡波特 和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描述了他們看到菲利普·羅斯、索爾·貝婁和辛西婭·奧齊克等猶太同齡人時的感受。 在那個時期的著作中,他們和其他著名作家認為,強大的工業猶太人是他們任何事業停滯不前的原因。
許多在文學領域工作的真正傑出的猶太人也自覺地使用了這個詞,從出版社到文學雜誌再到學術界。 這些猶太人有時會開玩笑說他們在他們的行業中遇到了多少其他猶太人,或者表示沮喪,因為他們不在他們的圈內。
韋爾斯利學院猶太研究項目主任喬什·蘭伯特(Josh Lambert)在他的新書《文學黑手黨:猶太人、出版和戰後美國文學》中探討了“文學黑手黨”的奇怪現象,耶魯大學出版社本週出版. 該書取材於當時著名的猶太作家、編輯、出版商和學者,包括 Knopf 編輯 Harold Strauss、Esquire 編輯 Gordon Lish、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Lionel Trilling 和作家 Ann Birstein,消除了“文學黑手黨”的神話。” 但蘭伯特還認為,處於權力位置的猶太人可能傾向於幫助其他猶太人,因為他們的個人和職業網絡都是由猶太人組成的。
在這本書中,蘭伯特解開了這一時期的職業和個人關係,他稱之為“猶太文學選舉權”——以及這種影響網絡持續到現代的方式。
這次採訪已經壓縮和編輯。
JTA:讓我們從最廣泛的問題開始:是否存在“猶太文學黑手黨”? 如果有,那是什麼?
蘭伯特: 我認為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是,不,沒有,但無論如何談論它並不是無趣的。 杜魯門·卡波特認為那裡沒有猶太文學黑手黨,他說:“哦,這些人在詭計多端。” 甚至沒有猶太作家梅耶·萊文認為的猶太文學黑手黨,[他認為]人們聚在一起參加聚會並說,“我們永遠不會談論他的書。” 那沒有發生。
我認為更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嚴肅的人會談論這個? 為什麼這個想法、這個模因或比喻會持續 20 或 30 年? 我認為,對於任何從事新聞業或文化行業的人來說,答案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在這樣的任何行業工作了五分鐘,你可以說有些人過得更輕鬆,走得更順暢。 他們得到了幫助,他們有優勢,他們的投球被更快地接受了。 除此之外,你還與人建立了關係,他們會決定誰給了你做事的機會或誰幫助了你。
很容易想像為什麼一個站在錯誤一邊的人,在某些時候,會覺得這不公平,覺得有什麼不對勁,覺得有問題。 所以這個“文學黑手黨”的比喻,只是人們表達對權力不當或不公平使用的感受的地方——就我的書而言,在出版業。
是否存在人們不當使用權力的情況? 當然。 我在書中談到了他們。 而且,我認為我們需要以一種更深思熟慮的方式來討論,這種力量、影響力、影響閱讀或出版內容的能力是什麼? 誰擁有它,他們如何使用這種權力?
您是一位研究猶太文化和猶太文學的學者,談論猶太人對出版業的影響。 在你的書中有一部分你只是列出了目前或曾經在出版業工作的猶太人。 當這可能會鼓勵對您所呈現的歷史進行反猶太主義閱讀時,為什麼要提請注意呢?
我認為,如果這本書和我的上一本書[“不潔的嘴唇:淫穢、猶太人和美國文化”]之間存在某種一致性,那就是這樣。 我不想把談話交給反猶分子,不管他們多麼強大或多麼可怕。 他們不應該是決定我們如何談論這些問題的人。
在我上一本關於淫穢的書裡,反猶分子以一種可怕的方式,以一種不恰當的方式,以一種有害的方式使用它。 [大衛杜克在推特上讚歎“不潔的嘴唇”,在一些反猶太主義出版物中被引用為猶太人是性侵犯者的“證據”。]我有點知道他們會這樣做。 他們可能會用這本書做到這一點。 問題是,我認為大衛杜克會做他所做的,不管我做什麼,所以我不會擔心這個。
但我確實認為我想與之交談的觀眾是美國的猶太人和關心文學體系的非猶太人,他們不是反猶主義者——我認為我們不能談論猶太人的成功、猶太人的影響力,猶太人的權力只會扭曲並且只會阻止我們理解重要且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那個清單:列出任何類型的猶太人都感覺有點奇怪。 但與此同時,否認它或假裝它不存在真的讓人感到不舒服。
你把戰後文學時期稱為“猶太文學選舉權”時期。 是什麼促使了這一點,以及這種突然提升猶太人在出版、雜誌和學術界的權力地位的利弊是什麼?
我一直在尋找一個術語,我喜歡“enfranchisement”,因為它不會告訴你一個人將要做什麼。 它只是說他們有一個新的機會和一種使用它的新方法。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一點,仍然很難與猶太人發生的其他社會經濟變化分開。 我們知道,在戰後時期,猶太人在經濟上做得更好。 以不同的方式在政治上對猶太人有更多的支持。 出版業的成功與這一切有關,但也與猶太人在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創立的這些公司的發展有關,這些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不歧視猶太僱員。
實際上真的很難理解 DIS選舉權看起來像,這並不意味著沒有一個猶太人可以發表任何東西,或者沒有一個猶太人可以做某事,而是真正意味著作為一般的事情,猶太人不在決策職位上。 而在戰後時期,從字面意義上來說,猶太人在該領域有任何工作變得完全不起眼。
你想一想:當這個特定少數群體中沒有一個人[現在]在這個行業擔任把關職能時,會發生什麼變化? 對於[猶太人擁有的出版社] Knopf 的編輯哈羅德·施特勞斯來說,答案是,一旦來自少數群體的人處於那個位置,他們就會對這個群體的身份是什麼,應該是什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他們的決策。 一大群猶太編輯有機會制定出版計劃並說,我認為這些是人們想要閱讀的書籍。 我認為這絕對是一個混合包。
[Knopf] 在翻譯意第緒語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為什麼它能夠做到這一點? 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高聲望的歐洲文學,他們可以呈現一些意第緒文學,不是血汗工廠的詩歌,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 同時,Knopf 比其他一些出版商更願意接受的部分內容, 因為 那是一座猶太人的房子,我認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看到並說它是反猶太主義的。 像 HL Mencken 這樣的人寫了幾段關於猶太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群體的文章。
這幾乎就像,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作為猶太人的身份,他們覺得他們更像是可以發表一些這種反猶太主義的作品,以此來避免人們指責他們是文學黑手黨的一部分。
您有章節講述了出版社中猶太人根深蒂固的厭女症和公然的裙帶關係實例。 猶太人可以從這些關於當時文學領袖失敗的編年史中吸取什麼教訓?
我會談談裙帶關係的文章,因為我認為這是它最清楚的地方的一部分。 裙帶關係是我們社會中的巨大力量。 如果你想想你的朋友,你認識的人,和你一起長大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有富有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西方文化普遍如此。 不同的是,三四代以前,大多數美國猶太人都無法指望這種遺產。 在過去的 20、30、40 年中,這種情況變得更加普遍。
它不是無處不在的。 不是美國猶太社區中的每個人,但就他們的優勢而言,它確實改變了猶太人相對於美國其他人的位置。 你想用你被賦予的優勢、特權和權力做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同意,對於一個書呆子的年輕猶太人來說,找到一份出版工作要容易得多,在那個職業上取得成功,而且我們關心更大的社會正義問題,我認為這會促使我們想要問一些問題,例如,我們能做什麼?
作為父母,我知道:我愛我的孩子。 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不成功。 但我確實想創建的系統並不是說最享有特權的人的孩子在任何情況下都將繼續成為最享有特權的人。
今年普利策小說獎得主, 約書亞·科恩的《內塔尼亞胡斯》, 是對美國猶太人生活和猶太人內部政治的極其具體的描繪。 這與您在菲利普·羅斯和索爾·貝婁以及所有其他在 50 年代贏得主要文學獎項的猶太人的書中描繪的場景並無不同。 “猶太文學黑手黨”的想法還在我們身邊嗎?
毫無疑問,猶太人仍然是傑出的、成功的和繁榮的。 如果你給我三個想要從事出版業工作的大學生,一個是猶太孩子,我的錢會花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最有可能成功——因為他們的人脈最多,等等。
普利策的決定,當這樣的獎項發生時,感覺就像它告訴你一些關於文化時刻的事情。 普利策委員會公開了該小組的評委姓名,該小組將獎項授予喬什科恩的書。 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將其視為普利策獎,而是將其視為發生在這三四個人之間的對話。 我們對他們了解多少以及他們的興趣是什麼? [2022 年小說普利策獎的評審團成員包括懷廷基金會主任考特尼·霍德爾、柯克斯評論主編湯姆·比爾、華爾街日報小說專欄作家薩姆·薩克斯、西北大學教授克里斯·阿巴尼和赫斯頓/賴特前主任黛博拉·赫德基金會支持黑人作家。]
獎項絕不是一本書的客觀或純粹代表。 它始終只是一個關於一群人以及他們在特定時刻興奮什麼的故事。
這是一個元問題:作為出版領域的猶太學者,你談到了你能夠利用自己的關係來出版這本書,而我採訪你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彼此了解其他通過類似的空間:你是我的研究生導師,後來我參加了你舉辦的猶太寫作獎學金。 當你在世界和你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航行時,你是如何看待這些關係的?
我真的很感激這個問題,因為我只是認為,在更大的層面上,這就是我希望這本書思考的問題。 一,更多的透明度是好的。 我們應該說我們彼此認識,這很好。 我不認為你要發表一篇關於我的書的文章不可能是腐敗的,或者是嚴重錯誤的跡象。 但公平地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幫你一個忙,而且我可能會,如果你能幫我一個忙,我將不勝感激。
我確實覺得當你更加關注這一點時,它應該會對你的行為方式以及你如何部署你所積累的任何力量產生影響。 Wellesley 擁有的一件事就是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校友網絡,來自學校的校友們真的被幫助當代學生的想法所驅使。 我對他們說,值得思考該校友網絡與哈佛校友網絡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 因為如果您的校友網絡所做的是讓那些享有特權並最有權獲得權力的人獲得額外的權力,那麼您可能會認為這不是最好的支持。 但是,如果您正在考慮女性和非二元性人群在傳統上和持續存在的代表性不足和歧視的行業,而韋爾斯利校友網絡可以幫助推動這些領域的更多正義和公平,那麼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就我作為學生的導師和支持者的角色而言,我正在努力思考:誰是最不可能獲得幫助的學生? 支持他們甚至可能不是我的本能,因為他們可能看起來與我不太相似,或者他們的目標可能與我不太一致。 但是我可以嘗試找到一種方法來利用我所擁有的任何優勢來幫助他們——為我在推薦信方面幫助的人、我試圖為他們提供機會的人帶來一種責任感,諸如此類。
您爭辯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文學黑手黨”,並且您概述瞭如果突然有大量黑人在這些出版權職位或其他邊緣化群體中出現,20 年、30 年後會是什麼樣子,以及這可能會如何影響猶太人也一樣。 你能把它分解嗎?
如果我們都承認猶太人扮演了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超大角色,並且直到現在,他們還在出版業中扮演了這個角色,那麼你可以從中學到的一件事是,如果一個群體擁有相當不成比例的角色,那實際上是可以的力量。
有一個多元化的概念,這意味著你在這個行業的比例應該與你在人口中的比例相關。 我只是不認為工業是這樣運作的,權力也不是那樣運作的。 你想看到的不是一種對多樣性進行標記化的方法,它需要幾個人並將他們置於權力位置,而是一種真正的轉變,在那裡可以感覺到永遠不會有太多人。
而且我認為它正在以一種非常強大和有趣的方式發生在出版業中。 自從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以來,就有了一場運動,真正關注美國文化中的白人至上主義。 出版業聘請了一些非裔美國人擔任非常重要的職位。 我認為這很棒。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希望猶太人的歷史表明,在他們僱傭了那些重要職位的傑出人物之後,他們應該再僱傭 400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