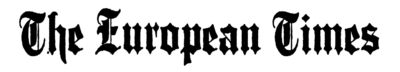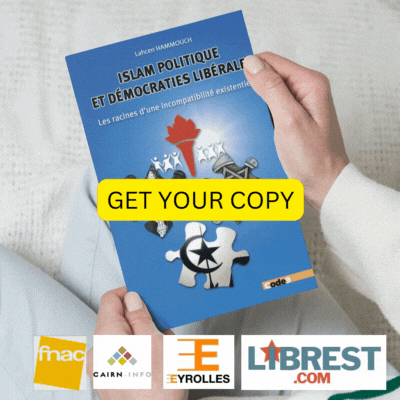特奧多·德切夫
本分析的前一部分題為“薩赫勒——衝突、政變和移民炸彈”,討論了西非恐怖活動的興起以及無法結束伊斯蘭激進分子在馬里和布吉納法索對政府軍發動的遊擊戰的問題法索、尼日、查德和奈及利亞。 會議也討論了中非共和國持續內戰的問題。
重要結論之一是,衝突的加劇充滿了「移民炸彈」的高風險,這將導致整個歐盟南部邊境面臨前所未有的移民壓力。 一個重要的情況是俄羅斯外交政策有可能操縱馬利、布吉納法索、查德和中非共和國等國家的衝突強度。 [39] 莫斯科將手放在潛在移民爆炸的「櫃檯」上,很容易對那些通常已被視為敵對的歐盟國家施加誘導移民壓力。
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富拉尼人發揮了特殊作用。富拉尼人是一個半游牧民族,是遷徙牲畜飼養者,居住在從幾內亞灣到紅海的地帶,根據各種數據,人口數量為30 至35 萬。 。 作為歷史上在伊斯蘭教向非洲尤其是西非的滲透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富拉尼人對伊斯蘭激進分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儘管他們自稱伊斯蘭教蘇菲派,這無疑是最重要的伊斯蘭教派。寬容,也是最神祕的。
不幸的是,從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問題不僅僅是宗教對立。 衝突不僅是種族宗教衝突。 它是社會、民族、宗教的,近年來,透過腐敗累積的財富轉化為牲畜所有權的影響——所謂的新畜牧主義——已經開始發揮額外的強大影響力。 這種現像是奈及利亞的特色,也是本分析第三部分的主題。
馬利中部的富拉尼人與聖戰主義:變革、社會叛亂與激進化之間
雖然2013年「藪貓行動」成功擊退了佔領馬利北部的聖戰分子,「巴爾漢行動」則阻止他們返回前線,迫使他們躲藏起來,但襲擊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蔓延到了馬裡中部地區。馬利(尼日河拐彎處地區,又稱馬西納)。 整體而言,2015年以後恐怖攻擊增加。
聖戰士肯定無法像 2012 年在馬利北部那樣控制該地區,並被迫躲藏起來。 他們並沒有“壟斷暴力”,因為民兵是為了對抗他們而成立的,有時還得到當局的支持。 然而,有針對性的襲擊和殺戮正在增加,不安全局勢已達到該地區不再由政府真正控制的程度。 許多公務員離職,大量學校關閉,一些城市最近的總統選舉無法舉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情況就是北韓「傳染」的結果。 聖戰武裝團體在未能建立獨立國家後控制了幾個月的北部城市,被迫“更加謹慎行事”,被趕出北部城市,尋找新戰略和新運作方式,從而能夠採取行動。利用中部地區不穩定因素獲得新的影響力。
其中一些因素對於中部和北部地區來說是共同的。 然而,如果認為2015年後馬利中部地區頻繁發生的嚴重事件只是北部衝突的延續,那就錯了。
事實上,其他弱點更為中部地區所特有。 當地社區被聖戰士利用的目標各不相同。 雖然北部的圖阿雷格人聲稱阿扎瓦德獨立(這個地區實際上是神話般的——它從未與過去的任何政治實體相對應,但對於圖阿雷格人來說,它分開了馬利北部的所有地區),但代表的社區中部地區並沒有提出類似的政治主張,就其所提出的任何主張而言。
所有觀察家都強調富拉尼人在北部事件和中部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之間的差異,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事實上,馬西納解放陣線(最重要的武裝團體)的創始人哈瑪德·庫法(Hamadoun Kufa)是富拉尼族人,他的絕大多數戰士也是富拉尼族人,他於28 年2018 月38 日被殺。 [XNUMX]
富拉尼人在北部很少,但在中部地區人數眾多,和大多數其他社區一樣,他們擔心該地區流動牧民和定居農民之間的競爭加劇,由於歷史和文化環境,他們受到的影響更大。
該地區和整個薩赫勒地區的決定性趨勢導致遊牧民族和定居者難以共存,其本質上有兩個:
• 薩赫勒地區已經發生氣候變遷(過去 20 年降雨量減少了 40%),迫使遊牧民族尋找新的牧場;
• 人口成長迫使農民尋找新的土地,這對這個人口已經稠密的地區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38]
如果富拉尼人作為遷徙牧民對這些發展帶來的族群間競爭特別困擾,那麼一方面是因為這種競爭使他們與幾乎所有其他社區(該地區是富拉尼族、塔馬謝克族、桑海族)的家園。 、博佐人、班巴拉人和多貢人),另一方面,因為富拉尼人尤其受到與國家政策更多相關的其他發展的影響:
• 即使馬利當局與其他國家不同,從未對定居的利益或必要性問題進行理論論證,但事實是,發展項目更多地針對定居人民。 大多數情況下,這是由於捐助者的壓力,通常支持放棄游牧主義,認為與現代國家建設不太相容,並且限制了受教育的機會;
• 1999 年實行權力下放和市政選舉,儘管這為富拉尼人民提供了將社區訴求提到政治舞台的機會,但主要促成了新精英的出現,從而對傳統結構提出了質疑。習俗、歷史和宗教。 富拉尼人對這些轉變的感受尤其強烈,因為他們社區的社會關係是古老的。 這些變化也是由國家發起的,他們一直認為國家是從外部「進口」的,是與他們自己相去甚遠的西方文化的產物。 [38]
當然,這種影響在分權政策的變遷中是有限的。 然而,這在許多城市都是事實。 毫無疑問,這種轉變的「感覺」比其實際影響更強烈,尤其是在富拉尼人中,他們傾向於認為自己是這項政策的「受害者」。
最後,歷史記憶不應被忽視,但也不應被高估。 在富拉尼人的想像中,馬西納帝國(莫普提為首都)代表了馬利中部地區的黃金時代。 除了社區特有的社會結構和對宗教的某種態度之外,這個帝國的遺產還包括:富拉尼人生活並認為自己是純粹伊斯蘭教的支持者,在誇德里亞的蘇菲派兄弟氛圍中,對嚴格的宗教信仰敏感。應用《古蘭經》的禁令。
馬西納帝國領導人所宣揚的聖戰與目前在馬利活動的恐怖分子所宣揚的聖戰不同(他們將訊息傳達給其他穆斯林,而這些穆斯林的做法被認為不符合建國文本)。 庫法對於馬西納帝國的領導人物的態度是曖昧的。 他經常提到他們,但他再次褻瀆了塞庫·阿馬杜的陵墓。 然而,富拉尼人信奉的伊斯蘭教似乎與聖戰組織經常聲稱屬於自己的薩拉菲主義的某些方面存在潛在的兼容性。 [2]
2019年,馬利中部地區似乎正在出現一種新趨勢:加入純粹當地聖戰組織的最初動機逐漸變得更加意識形態化,這一趨勢反映在對馬利國家和現代性的質疑上。 聖戰宣傳宣稱拒絕國家控制(西方強加的,而西方是其中的同謀),並從殖民化和現代國家產生的社會等級制度中解放出來,與其他民族相比,富拉尼人在富拉尼人中得到了更「自然」的回應。團體。 [38]
薩赫勒地區富拉尼問題的區域化
衝突擴大到布吉納法索
富拉尼人在布吉納法索薩赫勒地區佔多數,該地區與馬利接壤(特別是與莫普提、廷巴克圖和加奧地區接壤的蘇姆省(吉博省)、塞諾省(多里省)和瓦德蘭省(戈羅姆-古姆省)馬利)。 以及尼日的泰拉和蒂拉貝里地區。 瓦加杜古也有一個強大的富拉尼社區,佔據了達波亞和哈姆達拉耶社區的大部分地區。
2016年底,布吉納法索出現了一個自稱屬於伊斯蘭國的新武裝組織-Ansarul Al Islamia或Ansarul Islam,其主要領導人是富拉尼傳教士馬拉姆·易卜拉欣·迪科( Malam Ibrahim Dicko),他與馬利中部的哈瑪德·庫法(Hamadoun Koufa)一樣,透過對布吉納法索國防和安全部隊以及蘇姆省、塞諾省和刪除省學校的多次襲擊而出名。 [38] 2013年政府軍恢復對馬利北部的控制期間,馬利武裝部隊抓獲了易卜拉欣·馬拉姆·迪科。 但在巴馬科富拉尼族領導人(包括前國民議會議長阿里·努胡姆·迪亞洛)的堅持下,他被釋放。
Ansarul Al Islamia 的領導者是來自中央的 MOJWA(西非統一與聖戰運動 – 西非統一與聖戰運動,「團結」應理解為「一神論」 – 伊斯蘭激進分子是極端一神論者)的前戰士。馬裡。 馬拉姆·易卜拉欣·迪科現已被推定死亡,他的兄弟賈法爾·迪科接替他成為伊斯蘭輔助者組織的領導人。 [38]
然而,該組織的行動目前仍受到地理限制。
但是,就像在馬利中部一樣,整個富拉尼社區被視為與聖戰士同謀,聖戰士的目標是定居社區。 為了應對恐怖攻擊,定居社區組成了自己的民兵來保衛自己。
因此,2019年1月上旬,為應對不明身份人員的武裝襲擊,伊爾古居民對富拉尼人聚居區進行了兩天(2月48日至41日)的襲擊,造成14人死亡。 警察出動以恢復平靜。 同時,在幾英里外的Bankass Cercle(馬里莫普提地區的一個行政區),42 名富拉尼人被多貢人殺害。 [XNUMX], [XNUMX]
尼日局勢
與布吉納法索不同,尼日爾沒有恐怖組織在其領土上活動,儘管博科聖地試圖在邊境地區,特別是在迪法一側建立自己的勢力,以贏得那些認為該國經濟狀況剝奪了他們未來的年輕尼日爾人的支持。 。 到目前為止,尼日已經能夠反擊這些企圖。
這些相對成功的具體原因是尼日當局對安全問題的重視。 他們將國家預算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給他們。 尼日爾當局已撥出大量資金來加強軍隊和警察。 這項評估是考慮到尼日爾現有的機會而做出的。 尼日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墊底),很難將支持安全的努力與啟動安全政策結合起來。發展過程。
尼日利亞當局非常積極地進行區域合作(特別是與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合作打擊博科聖地),並且非常願意接受西方國家(法國、美國、德國、義大利)在其領土上提供的外國軍隊。
此外,尼日爾當局不僅比馬利當局更成功地採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圖阿雷格人問題,而且對富拉尼問題也比馬利當局更加關注。
然而,尼日爾無法完全避免來自鄰國的恐怖蔓延。 該國經常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攻擊發生在東南部與奈及利亞接壤的邊境地區,以及西部靠近馬利的地區。 這些都是來自外部的襲擊——博科聖地在東南部領導的行動以及來自西部梅納卡地區的行動,該地區是馬裡圖阿雷格叛亂的「特權滋生地」。
來自馬裡的襲擊者通常是富拉尼人。 他們沒有博科聖地那樣的力量,但由於邊境的孔隙率很高,因此更難阻止他們的攻擊。 參與襲擊的許多富拉尼人都是尼日爾人或有尼日爾血統——1990 世紀38 年代,蒂拉貝里地區的灌溉土地開發減少了他們的牧場,許多富拉尼移徙牧民被迫離開尼日爾並在鄰國馬裡定居。 [XNUMX]
此後,他們捲入了馬裡富拉尼人和圖阿雷格人(伊馬哈德人和道薩基人)之間的衝突。 自從馬裡上次圖阿雷格人起義以來,兩個群體之間的力量平衡發生了變化。 那時,自1963年以來已經多次叛亂的圖阿雷格人已經掌握了許多武器。
2009 年,當甘達伊佐民兵成立時,尼日的富拉尼人就被「軍事化」了。(這個武裝民兵的成立是歷史上較老的民兵組織「甘達錦鯉」不斷分裂的結果, 「甘達伊佐」與「甘達伊佐」民兵是同一支民兵)。由於「甘達伊佐」旨在對抗圖阿雷格人,富拉尼人加入了它(馬裡富拉尼人和尼日爾富拉尼人),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整合到MOJWA(西非統一與聖戰運動–團結運動(一神論)和西非聖戰),然後是 ISGS(大撒哈拉伊斯蘭國)。[38]
圖阿雷格人和道薩基人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富拉尼人之間的權力平衡正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到 2019 年已經更加平衡。 結果,新的衝突發生,往往導致雙方數十人死亡。 在這些小衝突中,國際反恐部隊(特別是在「巴爾漢行動」期間)有時與圖阿雷格人和道薩克人(特別是與馬利安全軍)建立了臨時聯盟,後者在與馬裡政府締結和平協議後參與了打擊恐怖主義。
幾內亞的富拉尼人
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是唯一一個富拉尼人是最大族群但不是多數的國家,約佔總人口的 38%。 儘管他們來自幾內亞中部,該國的中部地區,包括馬穆、皮塔、拉貝和高阿爾等城市,但他們也出現在他們為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而遷徙的所有其他地區。
該地區並未受到聖戰主義的影響,除了流動牧民與定居者之間的傳統衝突外,富拉尼人沒有也沒有特別參與暴力衝突。
在幾內亞,富拉尼人控制著全國大部分經濟力量,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宗教力量。 他們是教育程度最高的。 他們很早就識字了,首先是阿拉伯語,然後透過法國學校學習法語。 伊瑪目、《古蘭經》教師、來自國內和僑民的高級官員中,富拉尼人佔大多數。 [38]
然而,我們可以對未來感到好奇,因為自獨立以來,富拉尼人一直是[政治]歧視的受害者,遠離政治權力。 其他族群感到受到這些傳統游牧民族的侵犯,他們來破壞他們最好的土地來建造最繁榮的企業和最耀眼的住宅區。 根據幾內亞其他民族的說法,如果富拉尼人掌權,他們將擁有所有權力,鑑於他們的心態,他們將能夠保留並永遠保留它。 幾內亞第一任總統塞庫·杜爾針對富拉尼族群發表的激烈敵對言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看法。
從1958年獨立鬥爭初期開始,來自馬林克人的塞庫·杜爾及其支持者就一直面對巴里迪亞萬杜的富拉尼人。 塞古·杜爾上台後,將所有重要職位都交給了馬林克人。 1960 年,特別是1976 年,所謂的富拉尼陰謀的曝光,為他消滅重要的富拉尼人物提供了藉口(特別是1976 年的特利·迪亞洛,他是非洲統一組織的第一任秘書長,一位備受尊敬和支持的人)。傑出人物,被監禁並剝奪食物,直到死在地牢中)。 這一所謂的陰謀為塞庫·杜爾提供了一個機會,他發表了三場演講,極其惡意地譴責富拉尼人,稱他們為“只想著金錢……”的“叛徒”。 [38]
2010年首屆民主選舉中,富拉尼族候選人塞盧·達萊因·迪亞洛在第一輪中拔得頭籌,但在第二輪各族群聯合起來阻止他成為總統,將權力交給了出身阿爾法·孔戴。馬林克人。
這種情況對富拉尼人民越來越不利,最近的民主化(2010 年選舉)使他們產生了公開表達的沮喪和失望。
2020 年的下一次總統選舉將是富拉尼族與其他民族發展關係的重要最後期限,阿爾法·孔戴將無法競選連任(憲法禁止總統連任兩屆以上)。幾內亞的少數民族社區。
一些臨時結論:
談論富拉尼人任何明顯的「聖戰主義」傾向都是極其傾向性的,更不用說這個民族前神權帝國的歷史所誘發的這種傾向了。
在分析富拉尼人站在激進伊斯蘭主義者這邊的風險時,富拉尼社會的複雜性常常被忽略。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深入探討富拉尼人的社會結構,但以馬利為例,它的社會結構非常複雜且等級森嚴。 富拉尼社會各組成部分的利益可能存在差異,並成為社區內行為衝突甚至分裂的原因,這是合乎邏輯的。
至於馬利中部,挑戰既定秩序的傾向據說促使許多富拉尼人加入聖戰士行列,有時是社區中年輕人違背成年人意願的結果。 同樣,年輕的富拉尼人有時會試圖利用市政選舉,正如所解釋的那樣,市政選舉常常被視為產生非傳統名人領導人的機會)——這些年輕人有時更多地將成年人視為這些傳統的參與者「名人」。 這為富拉尼人民之間的內部衝突(包括武裝衝突)創造了機會。 [38]
毫無疑問,富拉尼人傾向於與既定秩序的反對者結盟——這是遊牧民族與生俱來的。 此外,由於地理上的分散,他們注定永遠處於少數,因而無法對他們所居住的國家的命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即使他們似乎有這樣的機會,並相信他們可以透過這種機會來決定性地影響他們所居住的國家的命運。是合法的,就像幾內亞的情況一樣。
這種事態產生的主觀看法助長了富拉尼人在遇到麻煩時學會培養的機會主義——當他們面對那些將他們視為威脅性異物的誹謗者時,他們卻學會了培養這種機會主義。 他們自己作為受害者生活,受到歧視並註定被邊緣化。
第三部分如下
使用的來源:
分析的第一部分和當前第二部分中使用的文獻的完整列表在以“薩赫勒——衝突、政變和移民炸彈”為標題發表的分析的第一部分的末尾給出。 這裡僅給出分析第二部分所引用的來源—「西非的富拉尼和「聖戰主義」」。
[2] Dechev,Teodor Danailov,「雙底」還是「精神分裂症分叉」? 一些恐怖組織活動中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動機之間的相互作用,Sp。 政治與安全; 第一年; 不。 2; 2017年; 第 34 – 51 頁,ISSN 2535-0358 (保加利亞語)。
[14] Cline, Lawrence E.,薩赫勒聖戰運動:富拉尼人的崛起?,2021 年 35 月,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1 (1),第 17-XNUMX 頁
[38]桑加雷、布卡里、薩赫勒和西非國家的富拉尼人和聖戰主義,8年2019月XNUMX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和薩赫勒觀察站,戰略研究基金會(FRS)
[39] 蘇凡中心特別報告,瓦格納集團:私人軍隊的演變,Jason Blazakis、Colin P. Clarke、Naureen Chowdhury Fink、Sean Steinberg,蘇凡中心,2023 年 XNUMX 月
[42] Waicanjo,查爾斯,薩赫勒地區的跨國牧民衝突與社會不穩定,21 年 2020 月 XNUMX 日,非洲自由報。
攝影:Kureng Workx:https://www.pexels.com/photo/a-man-in-red-traditional-clothing-takeing-photo-of-a-man-13033077/